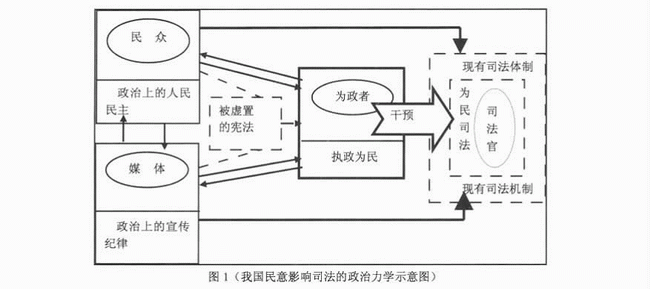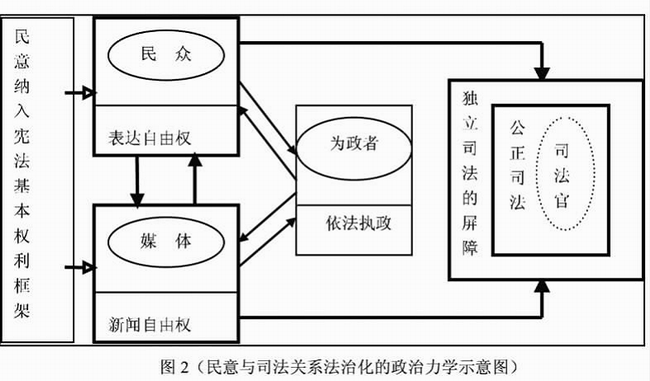摘要:本文着重考察“公案”这类特定案件的司法过程,从中观察和分析中国司法的政治力学现象。文章分析了民众、媒体、为政者和司法官四个主体及其相互间的角力关系,分析了民意对司法的影响,分析了司法与媒体的关系。认为司法与民意、媒体的角力,不能仅仅基于司法独立原则,而应当强调被告公平受审权。总之,司法的政治力学现象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司法的政治角力应当加以规制;通过制度设计,有的关系可以回归到权利与义务的关系,不仅会有更好的法律效果,还会有更好的社会效果。
关键词:公案司法;民众;媒体;为政者;政治力学
民意法庭是封闭的,而真正的法庭是开放的。[1]
——理查·马屈
尽管法律家往往与人民联合起来打击行政权,但法律家与行政权之间的自然亲和力,却远远大于法律家与人民之间的这种亲和力。[2]
——托克维尔
大多数案件的审判都属于典型的正常司法活动,但某些少数案件的审判,却是非典型的,因为它轰动全国、影响全社会。就案件的社会影响力而言,这类少数案件的影响力甚至比多数案件影响力的总和还要大。这类少数案件原本是很平常的案件,但由于某种特殊因素起作用,在社会上可以迅速演变成公共话题,引起媒体和民众的热烈评判,于是个案就成为公众议论的焦点和热点,我把它称为“公案”[3]。舆论对此给出了民意上的裁判,人们习惯于把这种情况称为“民意裁判”或“民意法庭”。本文所研究的司法的政治力学现象,着重考察(但不限于)演变为公案的那类案件。因为从法院角度来看,多数受干扰的案件是引起公众和舆论关注和议论的“焦点案件”和“热点案件”。而正是这类案件,恰恰折射出民主与法治的可喜进步和堪忧困境的双重形势。这就出现了连锁现象:涉及公案的司法过程中,出现了多个角力主体的介入,都基于政治的而非法律的理由参与到司法之中,导致了司法的“政治力学”现象。
一、四个角力的“审判者”
在西方所谓“高度曝光案件”(highly publicized cases)中,除案件当事人之外,通常存在着三个主体在发生影响作用,他们都可能单独地或联合地对公案进行“审判”,即民众、媒体和司法官。但是在中国,还有第四个角力的主体,它就是为政者。为了把问题分析得清楚一些,我只把对案件当事人产生影响的角力主体进行分析,这四个角力主体分别是民众,新闻传媒,为政者,司法官。虽然还有一个主体是法律专家[4],但考虑到本文分析的需要,我把这个主体合并人民众之内。民众、新闻传媒和为政者为什么掺和或参与到个案司法中来呢?这就要从个案演变成公案的过程说起。
究竟是先有公案,还是先有民意裁判,令人迷惑。但是我们可以很清楚地说,个案之所以引起热议和评判,成为公案,绝不是空穴来风,是因为它具有某种“主题元素”[5],比如贫富关系、权贵身份、道德底线等等。如果没有个案中所包含的这种“主题元素”,那么,个案是绝不会引起公众和媒体热议的,因而也成为不了公案。这个“主题元素”吸引了公众、媒体、为政者参与到个案的司法中来。正是这个“主题元素”,才成为公众、媒体和为政者不同程度地干预司法的合乎“目的正当”的理由。
自从进入互联网时代,互联网成为“舆情监视器”,网上投射着转型时代的冲突、困顿、无奈和焦虑,有人说,顺着网线可以触摸时代的脉搏与心跳。可以肯定的是,网络目前已经成为民众通向政治的无形的、非正式的重要通道。在这样的新条件下,个案很容易演变成“公案”,民意法庭和民意公审也就在此出现了。民众、媒体等舆论构成了对个案进行审判的架势,这就是所谓的“民意法庭”,又称“舆论法庭”(The court of public opinion),它通过舆论和民意来进行审判,有意或无意地影响司法裁判。民意法庭一般有两个裁判者,即民众和媒体。从应然的理论上讲,民意法庭会对陪审团产生影响,但很难对没有陪审团制度的司法活动起影响作用,因为司法机关是独立行使职权的,并且法官的职业习惯往往对民意和舆论抱排斥态度。民意和舆论即使有影响,也是在法院不知不觉状态下产生的。但是如果通过为政者,则无庸置疑可以直接干预司法。
他们四方面力量构成的角力关系,都不是法律意义上的,而是政治意义上的。可以说这是一种“政治力学”问题。这里的政治力学并不是指通常的政治斗争,而是它们都利用法律或法律的弱点强调自己的意志,对司法施加压力,对案件当事人产生影响。其中,既存在多种主体角色本位的天然固有的力学关系—静态物体关系,比如固有的职业主义与民主主义的较量;同时,它们又与社会发展和法制改革相联系而产生连锁反应—这种力学关系又是动态的,这种力量强弱可能是阶段性的,因而是可以根据社会发展变化而权衡的。它们四方面有各自的正当性理由来支持,所以我们一时难以辨别谁对谁错。
眼下民意与司法这两者之间的正常关系出现了严重的扭曲,民众、媒体、为政者和司法官四方面的认识也缺乏规范性和统一性,他们是公案这个混沌问题中的四个主角,究竟谁是这些公案的真正裁判官?司法、民众、媒体、为政者四方之间存在着相当复杂的关系。其中对司法判决起决定作用的并非法官,而是“匿名者”。是不是存在“匿名审判”,有没有“双簧审判”?如果说西方国家的陪审团对司法判决产生外行人的重要影响的话,那他们是能看得见的决定者,可是我们的决定者是无形的、匿名的。美国人也会批评陪审团式的民主,我们却找不到这样的匿名者,更谈不上当他们判断失误时去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6]。
让我们先简要地梳理以下六对角力关系及其隐藏着的政治力学。
1.民众与司法官。从民众角度来看,民众关注权利、关注司法、关注法律、关注法治,是好现象,这种现象显然说明民众有了解审判、参与审判的欲望和需求。但是,民意对司法的强烈关注和反应的同时,又包含有对司法不信任甚至仇官、仇权(权力)和仇法的心理。再者,民意的聚集可以影响和左右司法。有学者认为“实际上民意并不构成对司法独立性的损害”[7]。孤立地看这句话是对的,可是民意不影响司法不等于民意表达方式不会影响司法独立性。我国现行《宪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的“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8]那么民众舆论和新闻媒体是否可以干涉司法呢?这个问题在宪法上还没有解决。从司法官角度来看,一方面,司法职业化和专业化的发展,使得民众与司法官形成专业性间隔。另一方面,目前司法机关或司法官又有三种不良表现:“害怕”民意、讨好民意、无视民意。害怕民意就是担心得罪民意,因为我们历来有“民意不可违”的观念,否则会引起“司法民主问题”、“为人民司法还是为谁司法”问题。讨好民意就是迁就民众的不符合法律的要求,宁愿作和事佬,为尽量满足民众的法外要求而不惜扭曲法律甚至违背法律。但在有的场合,司法官顾不上民意,高高在上,脸难看,门难进,甚至民众告状难,诉讼权利得不到保护,陪审员形同虚设,等等。
2.媒体与司法官。司法官俨然以司法独立(我国司法官常用的理由)或公平审判(美英等国)为由,本能地排斥媒体;而媒体则以新闻自由或言论自由为由介入司法事务的报道。那么,在媒体与司法的优先次序关系上,孰先孰后?这在我们国家是个未决的、缺乏理论的问题。现在的困境主要集中于五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倾向性舆论是否对审判构成危害性?二是在判决前程序中,是否可对公众的知情权作适当限制,以及选择何种报道方式(是否允许现场直播),这也是目前没有得到解决的。三是媒体对审理后的判决加以评论是否妨害司法权威?过去,我们总是认为法院判决需要大家去维护,正象维护党和国家的权威一样。可是媒体并不以为然,有的认为只要不煽动对抗法律的执行就行。四是由谁作出规定对媒体施以约束?我国目前尚无新闻法、传媒法等,记者职业道德规范也很不健全。这是导致混沌局面的另一原因。五是以何种方式来协调新闻自由和公平审判的关系?既保障新闻自由,又保障公平审判?
3.民众与媒体。某种意义上说,“新闻媒体的监督,实质上是民众的监督”这话不假[9]。民意的载体或形式有哪些?来信来访、互联网(BBS、转贴、博客、E-mail等等)、大(小)字报、匿名信、手机短信、标语(包括横幅或对联)、报纸、电视、电台、广播……。其中最有效的载体是上访和互联网两种手段。前者有数千年历史,后者是最现代的方式,但对于引起为政者重视、影响司法判断来说,两者都很有效。民众交替结合地利用上访和媒体来传达民意,同时,媒体又刺激和煽动民意。在公众与媒体关系上,大多表现为一种“联姻”状态,无论是媒体正当的社会批判还是新闻商品的制造,客观上都追求迎合大众的效果,所以他们两者必然是有意无意地合奏或交响。特别是互联网媒体,它对于民众来说是一个最自由的区域,网络被称为“三个进不去”,即基层党组织“进不去”,思想政治工作“进不去”,公安、武警等国家强制力“进不去”,说明“网上群体性事件”的处置手段极为缺乏。[10]
4.为政者与媒体。我们的为政者对媒体的态度是一直把它作为党和政府的“耳目喉舌”,[11]出现互联网等新媒体以后,情况就发生了很大变化。目前还没有制定新闻传播法,因此依靠党内宣传部门加上政府的行政手段来管理传媒。管理和控制网络媒体是一个伤脑筋的事,于是想出了网络安全管制甚至“网络实名制”等办法。有时,媒体与为政者的关系是互相合作并交叉影响;有时,为政者可以控制并利用媒体,而媒体则挑拨并刺激为政者。最后都是通过为政者手中的权力来实现他们的默契合作的意图。至于为政者对于媒体是否影响司法的问题,还没有被提到议事日程,因为压根就没有被引起重视。在美国,民意与司法的角力关系中,民意的实际力量来自媒体;而在中国,民意的实际力量来自为政者。这就是我们所面对的问题的国情差别。
5.民众与为政者。古人把他们比作水与舟的关系(“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当代有名言曰“天下为公”、“执政为民”。当下为政者有两大要务,一曰改革发展,一曰稳定和谐。然而后者是前者的前提。因为“稳定压倒一切”,所以要确保安定团结与社会稳定问题是地方各级为政者的铁的纪律和任务。稳定问题成了某些地方为政者的心病和软肋。民众针对某些地方为政者的“软肋”,通过影响当政者来影响司法,找敏感时间和地点去上访、申诉、上网发帖、BBS等等,甚至发动“舆论性群体事件”。某些地方当局或领导会挟民意来命令甚至以各种方式强压司法机关。通常是领导很重视涉法涉诉的民意,它涉及到政治影响和社会稳定,所以通过政治组织的程序压下来,一直压到检察院和法院。
6.为政者与司法官。目前的一些地方为政者出于社会稳定和谐的目的,基于执政为民和司法为民立场,利用民意和媒体舆论,对司法施加了影响。当下这种“影响”并不是以往的那种“干预”方式,而是十分巧妙和隐蔽的。这种影响力主体在司法文书中看不到记载,因此被称为司法的“匿名者”[12]。有学者专门例举了夹江打假案、张金柱案、綦江彩虹桥垮塌案、孙志刚案、“宝马撞人案”、许霆案、彭宇案、三鹿奶粉案等公案中的“领导”批示或发话的情节。[13]民意和舆论并不会自动起作用,是被拿来用的。“实际上,在缺乏表达自由和新闻自由的情况下,舆论还远远没有强大到足以杀人的程度。决定这些热点案件的结果的,不是该案件的法官,也不是关注该案件的民众,而是那些拥有权力的匿名者。地方当政者通过民意挟持了司法”[14]。人民民主、执政为民、言论与新闻自由、司法独立,这四条原则在同一个问题上汇合了,这也或多或少构成了我们的宪政格局,也只有在宪政的框架内才能得以协调统一。司法与民意关系失衡,是因为除司法之外的其他三方(民众、媒体和为政者)在民主、民本或民主主义这一点上是一致的,是合力关系,他们是基于自然理性而形成了共同意志和共同话语的,正常情况下,他们的自然理性与司法的技术理性构成了角力关系。然而,目前司法官与律师没有形成职业共同体,其技术理性也没有确立并统一起来,势单力薄,所以不足以与民众、为政者及媒体的作用力相匹配。
图1所表现的司法领域受到民众、媒体和为政者三种力量的干预和影响,其中最大的力量是为政者。现有司法体制和司法机制无法阻隔外部的三种力量。图2所表现的司法领域受到民众和媒体两种力量的干预和影响,而为政者在通常情况下不对司法领域产生影响力,司法部门建立起独立的司法体制和机制,成为一个阻隔外力干预的屏障。
二、民意影响司法产生哪些效应
从理论上笼统地说,司法机关是能够正确对待法律与民意的。换言之,审判权都掌控在法院法官手里,怎么可能会受民意支配和影响呢?但在实践中,司法机关在审理这种“公案”性质的案件时,民意伴随和搀和(Intermingle,之所以用这个词,是因为民众大都发表有公共主题元素的善意议论,而并非无故恶意起哄干涉司法)在司法的全过程,应当承认,这不是民意的错。我们要承认,没有错误的民意,只有被理解错误的民意,以及被以错误方式运用的民意。常常出现的是司法容易受民意的干预(此处“干预”一词没有贬义,更应该把它作中性的理解,正如心理学上的干预)。因为一旦陷入公案,检察院和法院因种种原因,对民意的抗干扰能力也就降弱了。
这个问题确实是一片混沌状态,不管怎么样,我们得先行考察当下公案中民意影响司法的各种效应。根据民意对司法有无影响及其影响大小,我把它们大致分为八种情形,我所使用的案例大多数是已审结的公案。
1.民意无法从道德情感上接受法律的逻辑而干扰司法。例如“严禁刑讯逼供”、“刑讯逼供取得的证据无效”这样的证据规则和观念是被法律人广泛接受的职业逻辑。可是在“刘涌案”[15]中,民众面对刘涌这样犯有重罪的所谓“黑老大”,一时难以理解或难以接受“刑讯逼供取得的证据无效”这种法律规则。更准确地说,并非不能接受这种法律规则,而是不能接受这种规则首先用在一个黑社会头子身上[16]。
2.民意迫使司法判决体现民众的道德情感。比如四川泸州继承案受民意的搅扰导致法官不采纳遗嘱、不适用《继承法》的法律规则而适用了民法的基本原则。此案的民意几乎一边倒,支持发妻的继承权,而反对二奶的继承权。这是民众的一种朴素的道德情感。法官判决最受法律专家批评指责的地方在于:有法律规则的情况下适用了法律原则,这是存在方法论上的误区的。再比如“张金柱案”中汹涌的民意强烈要求法院严惩酒后驾车过失致人死亡的公安局副局长张金柱,张金柱身为公安干部,还酒后驾车,驾车还撞了人,撞了还逃逸,勾住被害人还拖了数里地,逃逸中还拖死了人,拖死的还是个教师,这教师还是个女教师……这都是根据朴素的道德情感来评论的,于是民意一口咬定“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最后导致犯交通肇事罪的张金柱最终被法院按照间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
3.民意不理解专业问题而仍然干预了司法的专业准确性。有的案件因法律问题的高度专业化而使民众无法深入理解。比如许霆案(恶意取款原审被判无期徒刑后改判为五年),在自动取款机上秘密取走不属于自己的款,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什么罪?如果是盗窃罪的话,是否构成盗窃金融机构罪?这是一个涉及法律解释的问题,涉及刑法条文在立法上是否合理的问题。因此,如此高度专业化的问题是民众难以讨论的,即使民众有兴趣讨论,也只是在立法范畴内的,而不是在司法范畴内的。可是,民意对此案的高潮迭起的呼声,使本案刑罚陡然从一审的无期徒刑降为二审的5年有期徒刑。
4.强烈的民意影响了司法程序。如刘涌案是因为民意的作用,导致二审结束后由最高人民法院提审;有的案件因民意的作用导致法院不敢判决,而多采取调解方式结案,比如南京的彭宇案。彭宇在公交车站扶起倒地的大妈并送其到医院就诊,大妈及其家人要求彭宇赔偿。彭宇是否推倒大妈的事实难以认定,但如果法院让彭宇赔偿则民意不答应。于是法院采取调解的办法了结此案,并以涉及当事人秘密为由而不公开调解结果的内容。这么复杂的案件,甚至可以说是个“疑难案件”,我们为法官捏了把汗,但在民意对司法的影响下,以调解结案,我们还算是为法官庆幸的。
5.民意有很强烈的压力,但司法仍然很独立地判断。“司法活动正确与否从来不取决于它是否得到公众的欢迎或是否符合大多数人的想法与做法。”[17]这种情形在中国法院也不乏其例。强烈的民意对司法确有压力,但由于司法机关坚持独立司法原则,因此民意并不对判决结果产生影响。比如杭州“胡斌五-七飙车案”的审理过程中,公众舆论喧嚣,但杭州西湖区法院仍然坚持不受影响,以事实为根据依现行刑法作了判决。尽管后来不少法律业内外人士认为现行刑法相关条款是不合理的,是需要修改的。但是也有这样的情形,在民意强烈的压力下,司法仍然很独立地判断,却导致不够合理的判决,比如被告崔英杰、宋金宁抢劫轮奸案。两被告对安顺市一名出身寒微的高中女生进行两次抢劫、两次轮奸,并以沉水和乱石捶砸两种方式残暴地杀死被害人,随后抛弃遗体于水库之中。该案的终审判决却是,崔英杰因坦白认罪态度较好而被课以死刑缓期执行。据报道,在让崔英杰免死的判决公布后,当地社会舆论和网民仍然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和抗议[18]。
6.民意影响了判决,导致良好的效果。比如,在另一个“崔英杰案”(街头小贩杀死城管队长不判死刑而判死缓)中,民意对以摆地摊为生的崔英杰抱有很深的同情心,并对野蛮执法的城管队长期抱有成见,因此希望法院从轻发落不判处极刑。律师的意见反映了民意并有事实为根据,办案的法官在搜查被告人住所时发现的一份能证明其极度贫穷的财产清单,与律师的意见形成印证,最后法官采纳了律师的观点—正反映了民意[19]。最后法院认为他不是非杀不可的,所以判死缓保住了崔英杰的头。这个结果的确更符合立法精神,也更体现法律的人本精神,更人性化。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这个案件不仅仅是民意的胜利,也是司法的胜利。本案所谓合理的方式就是律师的辩护和法院的证据材料,以及司法方法(法律解释与论证方法),推而广之,合理的方式应当是正当程序与法律方法。可见,通过正当程序和法律方法,合理的民意是可以被吸纳的。
7.民意促使个案中引发更深层问题的理论思考。比如陈凯歌诉胡戈“馒头血案”的诉讼,不仅在网络虚拟世界,还在现实世界都产生反响,此公案不仅限于著作权法上讨论的侵权是否构成的问题,还涉及到更多深层次的关于文化、艺术、网络与社会的法律问题的思考,季卫东教授对此作过发人深省的阐述[20]。另外,还有象“机场女工梁丽案”。在强大的民意之下,梁丽被检察院认定为“侵占罪”,因而,其法律责任追究问题就取决于被害人是否自诉。但不管本案结局如何,不少专家认为,“检察机关的处理结果存在一定的道德风险。梁丽的行为的确暴露出其法律意识的淡薄和道德的缺失。因此,有必要对社会的认知标准进行引导,让公众清醒地认识到法律上的免予公诉并非意味着道德上的‘豁免’,否则,法律的‘温情’将演变为对不当行为的纵容,进而混淆对行为认知和道德判断的标准,造成全社会难以承受的风险”[21]。
8.民意通过个案司法促进了制度的完善。比如“孙志刚案”中的民意促成了其公正办理,还推动了流浪乞讨人员管理与保障制度的完善。民意的参与,体现了法律上的监督的民主性、正当程序等价值,促进了司法的公开透明和公正性。2009年多起抗拆迁自杀案引起普遍的民意关注和呼吁,导致北大五位教授上书国务院,敦促修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这是另一例成功改变制度的典型案例。
民意对于司法和立法的影响,应当有所区分。民意对立法的影响是应该大力提倡的。立法本身是一场以民主价值为本位的活动,不民主的立法是失败的立法。但司法领域则不同,民意与司法的协调机制的设计,需要很认真地对待。陪审团制度是司法职业主义和司法平民主义的重要桥梁之一,不是唯一的办法,也未必是无可挑剔的。“相对于依照法律和证据,陪审团更多地是根据情感、偏见和同情心来决定案件,他们把审判转化成马戏团,在那里审判是由被告的衣着、种族或族裔来决定的”。[22]
此处所概括的八种情形,还只是表面现象。看起来是民意对司法的干预并产生了效应,为什么民意能够对司法产生影响呢?民意干预司法的背后都有些什么人参与?他们都有什么样的角力关系呢?这是我们要进一步分析的。
三、司法独立、慎待媒体,基于何种理由?
司法慎待媒体,基于何种理由?这是司法权在政治力学中的一个主要着力点,它关乎司法权能否独立运行。这个着力点的力量来自哪里,关系到司法权是否能够消解和匹敌对方力量。从世界各国实践来看,“司法独立”在根本上是与“言论自由”存在紧张关系或曰冲突关系的,这也就是说,司法机关的独立审判权与媒体的新闻自由权之间,具有天然的政治角力关系。我国法律界或法学界,在遇到民意关注司法或干扰司法时,常常误用“司法独立”为由来拒绝民众与媒体言论。司法警惕舆论是对的,但用“司法独立”这样的理由是否正当呢?我认为这不是正当的理由。为了说明这一点,让我们先从“司法独立”本身的理由说起。司法独立原则的提出已超过300年[23],为什么要司法独立呢?我们可以找到对理由的三种不同表述。
其一,权力关系的物理式机械构架,在国家若干种主要权力之间进行分配、分离、平衡、制约等等。比如德国人讲权力平衡(博林·布鲁克的权力平衡理论[24])和公民权利保障(奥托·迈耶认为司法权的任务即在保障人民权利,所以必须司法独立[25]),法国人讲权力分立(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钳制理论[26])美国人讲权力强弱对比(汉密尔顿的司法弱势论[27])。他们虽各自表述,但殊途同归,都是从国家权力结构的机械构造上来论述的,具有政治力学的显著特征。但是这种解释的理论触角没有延伸到司法独立与言论自由的关系问题。因为这种政治力学的理由只是针对国家权力而不是针对公民权利,也不针对社会权力。
其二,从受审判者的权利保障来论证司法独立,这也是物理力学意义上的。这主要表现在当代国际法上相关的司法独立原则的具体规定。比如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第10条规定:“人人完全平等地有权由一个独立而无偏倚的法庭进行公正的和公开的审讯,以确定他的权利和义务并判定对他的任何刑事指控。”联合国大会1966年12月16日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也明确规定:“在判定时对任何人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或确定他在一件诉讼案中的权利和义务时,人人有资格由依法设立的合格的、独立的和无偏倚的法庭进行公正的和公开的审讯。”还有其他国际性文件也都作了相似的规定[28]。
其三,从人的认识活动规律和特点人手。这种理由表述是非物理的,而是心理学意义上的。这是深入到司法权的思维特征中来揭示司法独立的理由的,最经典的表述是德国法学家拉德布鲁赫。他认为作为“认识”和“判断”的司法活动,“不容许在是非真假上用命令插手干预。‘学术自由’被用于实际的法律科学时,即成为‘法官的独立性’”[29]。“对法官而言法律规范则是目的本身,而且,在法官那里降临尘世的法律还不能受到异物的侵入:为使法官绝对服从法律,法律将法官从所有国家权力影响中解脱出来。‘只在仅仅服从法律的法院中,才能实现司法权的独立’”[30]。拉德布鲁赫揭示了司法权的思维特征,把它与学术自由作类比,认为它是认识活动,是判断活动,这是千真万确的。虽然拉德布鲁赫这两段表述仍然只是说明司法要排除权力、命令的插手和干预,并没有讲到司法权为什么要排除民众和媒体的干预,但是“思维容易受干扰”这条理由,可以用来解释这样的问题:司法为什么会与公民和媒体的言论自由相矛盾?
对司法独立的理由作心理学式的解释是有明显优点的。要不然,当我们碰到公民言论权与国家司法权交汇的时候,就可能陷入误区,可能分别会有两个完全不同的不妥当的判断:其一是“司法代表国家公权力,是公共事务,言论自由是公民权利的范畴,所以司法公权当然比公民私权更重要”。其二是我们可能会毫无顾忌地回答说:“因为言论自由是人民的基本权力要求,而司法独立代表国家的权力要求,因此,言论自由当然高于司法独立”。这样两种结论分别受两种截然对立的法意识形态的主导,其结论都太机械了,它们根本没有正视问题。
在此把我关于司法与媒体关系的观点整理为以下三点:
1.司法慎待媒体原则的双重理由。当司法与言论自由之间出现紧张关系时哪个优先?司法优先。理由是:第一,司法慎待媒体原则的适用应当充分考虑当事人的公平受审的权利。正是因为当事人有公正受审的权利,法院要保障这项权利才拒绝受干扰。第二,正是因为司法的思维特点容易受干扰才拒绝受干扰。法院应当从这两个问题来考量,来谨慎对待新闻媒体,并限制其对审判的言论监督。
2.司法慎待媒体原则不等于法院可一概拒绝媒体报道。新闻媒体对司法的监督,不能只取决于法院的态度。法院说不行,新闻媒体就不能监督司法了吗?言论与新闻自由的宪法性权利完全受制于法院的态度,显然也是不合理的。司法独立并不意味着媒体不能对司法进行报道。司法独立于政府、团体和个人,但不应当独立于媒体,至少“司法独立原则”在“言论和新闻自由原则”面前没有优越性[31]。
3.司法慎待媒体原则中应有之义是:要宽容甚至保护无恶意的错误言论。舆论对司法进行批评或评论时,难免出现非恶意的过激言词,所以司法机关应当对此抱着宽容的态度。“恰恰是在发生‘无恶意’的言论失实的时候,才更需要法律的保护,也是法律保护的价值所在”。[32]无恶意的言论表达是需要法律保障的,无恶意的言论在失实的时候更加需要法律保护。这一基本判断是基于对言论自由意义的认识—言论自由不仅施惠于我们大家这样的后果,而且还因为它是一个正义的政治社会基本的和构造上的特征。在这样的政治社会中,政府将它的成年公民看成是富有责任心的道德主体。[33]
当代西方司法界对于媒体进入法庭的态度日益趋于宽容,多数法官赞成媒体进入法庭。中国的问题背景却完全不同。关于司法与媒体的关系问题,中国法院经历过“无问题”、“小问题”到“出问题”再到“简化问题”的四个阶段。“无问题”阶段就是50年代至80年代初,新闻媒体很少进法庭采访,如果需要则需经得法院同意,这种规定在数十年的司法实践中基本没出什么问题。“小问题”阶段是在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中期,司法与媒体的关系只是有点非冲突性的“小问题”而已,中央虽颁布了若干原则性意见,但都不是基于冲突而下达的,而是为了统一协调。[34]90年代后期,是我国新闻媒体事业得到最快速发展的时期。民众对媒体监督司法的要求在日益增长。公众对司法的信任度产生了问题,同时公众认为媒体代表民主、透明,代表民众参政。可是,如果新闻工作者的新闻职业道德不能满足要求的话,则不仅严重影响公平审判,而且严重威胁法庭的威严—这涉及法律权威和正义信仰。“许多记者在寻找情绪化的东西。可怕的在于法官挖鼻孔也会成为当天的新闻”[35]—这种情况在中国日趋严重。
那么,什么样的情况下可允许新闻媒体进入法庭?媒体对司法的监督到何种程度是合适的?等等,新问题和新争议不断涌现。于是有了肖扬院长时代的大力欢迎传媒监督司法的新举措—甚至连法庭现场直播也出现了[36]。媒体与司法这个原本就很复杂的问题,在我们的国情条件下变得异常复杂了。最高人民法院的态度也变得有些隐约的内在矛盾。一方面对媒体过于热情欢迎,以我国最高人民法院2009年12月8日的《关于人民法院接受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若干规定》为例,法院表现得非常民主和开放,开篇第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主动接受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第二条规定“对于社会关注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通过新闻发布会、记者招待会、新闻通稿、法院公报、互联网站等形式向新闻媒体及时发布相关信息”;第三条规定“审判场所座席不足的,应当优先保证媒体和当事人近亲属的需要”,还规定了“旁听席中设立媒体席”;第五条规定“新闻媒体因报道案件审理情况或者法院其他工作需要申请人民法院提供相关资料的,人民法院可以提供裁判文书复印件、庭审笔录、庭审录音录像、规范性文件、指导意见等。如有必要,也可以为媒体提供其他可以公开的背景资料和情况说明”。2010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还颁布《司法公开示范法院标准》,其中第5条规定“审判法庭设立媒体席,并设立同步庭审视频室”。被广大基层法院和法官认为是不切实际。
另一方面对媒体过于严厉。比如最高法院2009年的《关于人民法院接受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若干规定》,其中宣布对媒体违反规定的行为要追究法律责任。于是遭到媒体人的批评,认为“法院与媒体本来是被监督与监督的关系,而今最高法却对于监督者提出了种种情形声言要追究法律责任,这里明显有一种阻吓新闻媒体监督的意愿在其中”[37]。不少人质疑最高人民法院此举不妥,还有认为最高法院越俎代庖,作为被监督者无权对监督者的权限作出限制性规定。法院这一次又是在角力,但是不是妥当呢?
在我展开第四部分论述的时候,先阐明两点:第一,法院用什么理由来对新闻言论自由说话?新闻自由的宪法性基础是言论自由。新闻媒体舆论监督是民主的具体形式,所以各国司法机关不敢对媒体有所怠慢。我国司法机关曾经一度对媒体十分排斥,学界也支持法院的这种态度,采取的理由是“司法独立”,即用司法独立原则来对抗言论自由(新闻监督)—这并不是一个正当的理由。第二,这个《若干规定》的弱点在哪里?《若干规定》只看到审判权与媒体权的关系,而缺少了一个重要的主体及其权利—即几乎看不到诉讼当事人权利的影子。好象除法院与新闻媒体的权力互动之外,当事人好象根本不存在。在司法与媒体的关系中必须考虑另一个主体,即案件当事人。而当事人的公平受审权,显然被忽略了。
四、“政治角力”法律化
司法与民意及媒体的关系中呈现出来的都是政治现象和政治关系,属于“政治力学”,显得十分复杂。考察这种复杂关系的深层,其本质是权利冲突。诸如公民基本权利、原被告权利、媒体监督权等权利围绕着司法权而产生冲突演变成政治角力关系。我们可以通过权利配置,把前面那些复杂的政治角力关系还原为法律角力关系—法律上的权利关系。
在这个问题中,出现了四项权利间的冲突问题:媒体的言论权、公民的监督权、法院的独立审判权以及被告人被公正审判的权利。在张金柱案、刘涌案、邓贵大案、胡斌案等等公案的审判过程中,表面上充斥着媒体与民众的声讨和法院的无奈,但这背后实际上存在着四方面权利的冲突,如果不从权利冲突中获得解决冲突的原则和规则,那么,我们绝没有理由说公案中的强大舆论不会对法院造成压力和影响。
事实上,在西方国家,“高度曝光的案件”或“公案”的司法中也存在政治角力关系,只不过随着制度的健全,西方国家把这种政治角力关系法律化、规范化了。自从上个世纪初法庭照相机出现以来,是否允许照相机进入法庭,在美国已经角力了将近一个世纪。在美国人看来,言论自由是非常重要的原则,所以在司法与媒体的关系问题上不会存在“媒体可否报道和评论司法”的疑问,而是媒体以何种方式报道和评论司法的问题。1917年伊利诺伊州最高法院开创了禁止法庭照相机的先例,法院单方面限制宪法赋予的“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权利,如果用今天的观点来看,这样是否妥当?当然这个问题在当时和后来都是有争议的。1925年的Dayton镇的“猴戏审判”,居然采用了广播电台的法庭现场直播,1935年的“林白案”法庭中媒体的长驱直入,导致了法律家的反思和反对,于是ABA于1937年制订了全面禁止法庭照相机及收音机转播;到1952年这条禁令被修正为禁止电视摄影。[38]。但是随着社会民主化和科技化的进程,媒体与司法的政治角力在变迁中继续,1965年加州法院司法委员会通过980号准则,禁止媒体在法院开庭或休庭时进行拍照、录音和广播,到1997年又规定由法官自己决定是否允许拍照。近一个世纪以来,两者关系的规则也在发生变化,问题的焦点也日益突出—媒体舆论是否影响被告的受公平审判的权利?
要解释清楚这个问题,我先举一个美国的案例来说明四方权利的冲突关系。美国关于新闻自由与公正审判(Free Press V. Fair Trial)的著名案例就是1979年的Gannett v. DePasquale判例:美国最高法院以五比四判决宪法第六修正案规定审判公开的权利[39],并不属于大众或新闻界,而是属于被告。[40]大法官斯图尔特说,公开审判这一宪法权利是为被告而设置的,而不是为公众设置的权利,允许公众接触刑事案件审判,也是为了让公众目睹对被告的公正审判。本案被告要求预审时不让新闻界旁听,而公众与媒体要求参与审判和旁听是没有宪法依据的。因为美国刑事案件审判和控辩中的陪审团制度就已保障了公众参与审判的公共利益。
斯图尔特大法官在这里申明了一项重要的规则值得我们借鉴,这就是:当诉讼当事人要求不公开审判,以保护当事人公正审判权,联邦宪法本身没有给予媒体获得信息的权利。当我们遇到权利冲突时,能否交由当事人来决定呢?这也是诉讼当事人主义处分原则的体现,是他的权利就应该由他自己来处分。另外,鲍威尔法官认为,新闻界有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保护的旁听的权利,是因为新闻界是公众寻求信息的代理人。但新闻界的这一权利受到被告享有公正审判的宪法权利的限制。因此法院对竞争的两项宪法权利进行权衡:一是不受限制行使第一修正案的旁听权,是否严重威胁对被告人的公正审判;二是当被告要求法院不准公众旁听时,法院考虑是否有其他选择,在保障公正审判的同时,不严重干扰公众获得信息的权利。本案正是通过强调第六修正案的公开审判原则保障被告的人身权利,才据此禁止公众和媒体获得法庭审理信息的权利。[41]
通过这样的处理,其实就是以权利(权力)与义务(责任)的关系来处理,这里的效果不仅有了更好的法律效果,还有更好的社会效果。可见美国人也讲究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只是美国人通过制度把两种效果有机统一在一起了。
可见,在这个问题上其实存在着多方力量的对抗和角逐的“力学”关系。现在的问题很清楚地集中在这样的问题上—言论(新闻)自由与公平受审权利,两者之间孰先孰后?让我们看看美国亚里桑那大学哲学教授J·范伯格所讲的一个道理:请设想有这样一个早期的未成熟阶段的简单法律体系,它包含着一个法律规则,允许每个人有权在空中随意按任何方向和以任何速度挥动他的胳膊,并且它也包含这样的规则,允许每个人都有权不让鼻子受到拳击。假如,尼普打了塔克的鼻子,却在法院诉说他完全是在自己的权利范围内行事;与此同时,塔克则根据他的权利信念宣称,他的权利受到侵犯。这时法院应当翻阅和寻找立法者的立法原意,或者开始冷静地“造法”。这时,必然求诸于权益平衡程序,也就是常常指导立法者考虑问题的程序。人们会发现:被告挥动胳膊的权利是基于增进个人健康的目的,而受害者的个人权利却是个人面部避免痛苦和免遭损伤。这两种权利哪一项更要优先保护呢?可以证明,绝大多数人会把面部免受打击的权利看得重于运动四肢的权利。法院也当然地会发现,保护面部的权利比促使手臂强壮运动的权利更为重要—这一条款就是解决权利冲突中产生的规则,是权利规则的例外条款。[42]
美英等国在“备受关注案件”的审判中偏向于保护被告的权利[43]。但是英国与美国在实现这一目标的措施上存在不同:英国法院有抵制媒体舆论的倾向,而美国法院则有尊崇新闻自由的态度。这是两国间最大的前提性的差异。于是导致两国措施上的不同特点:英国以藐视法庭(制度)来控制倾向性舆论,严格限制媒体报道刑事司法的能力;英国法院认为,无限制的舆论报道对司法带来潜在的威胁。而美国并不直接控制舆论,而是通过控制陪审团来控制倾向性舆论,比如采取“对陪审团的广泛预先审核,完全隔离陪审团”等措施[44]。在美国人看来,英国的藐视法庭制度很不妥当地限制了媒体的新闻自由。当然,正如布兰德伍德所分析的,两国的措施都有各自的缺陷:美国无限制地公开报道使刑事被告无法得到公平审判,而英国在大力保护被告的同时,践踏了言论自由却实际上无法确保审判权得到妥当的保护,所以他建议美英两国都作些修正。包括:有目标地控制陪审团,当陪审员接触过不被法庭接受的证据,都被认定为存在偏见;法院发布限制法庭参与者(如律师)言论的禁令[45]。
其实从美国司法惯例来看,法院面对民意与司法的冲突关系、面对新闻自由与公平受审的冲突关系,除了有目标地控制陪审团、发布言论限制令之外,可选择的措施还有:隔离陪审团、移送管辖、延期诉讼、不公开审理,甚至对已作的判决予以撤销。[46]这都是用法律角力来代替政治角力的具体措施。
然而,我国诉讼法里面没有“公平受审权”,备受关注的公案审判中,我们的法官和大众一样似乎很不在意被告人公平受审的权利,更没有什么措施来保护公平受审的权利,这不能不说是一大制度缺陷。
余论
司法的政治力学现象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司法的政治角力应当加以规制和克俭,有的关系是完全可以回归到法律关系上来的,设计成司法体制和机制,并且以权利(权力)与义务(责任)的关系来处理,不仅会有更好的法律效果,还会有更好的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
为政者关心、尊重和爱护民意,是民主政治的进步,也是法治社会的进步。我们也能够理解,在制度不健全不合理的情况下,为政者出面角力或矫正都是具有迫不得已的合理性。但是对司法中的民意的关心、尊重和爱护是有特殊方式的。本文虽然讨论政治力学问题,却把最典型、最有力的政治角力主体—为政者有意识地放在一边。其实,并不是不关注它,而是在制度和规则不健全的情况下,无法对为政者干预司法的行为作出肯定或否定的意见。如果我们的司法制度,已经对各种政治角力关系作了合理的制度安排的话,那么为政者对司法的角力或矫正作用也就可以忽略甚至消除了。
如果没有为政者的批示,则民意与司法的关系通过言论自由与公平审判的角力,他们基本上是能够平衡的。媒体的新闻自由与公平审判之间通过相互的角力,也是可以自动趋于平衡的。因此,在没有为政者的力量介入的情况下,司法官考虑民意是有正当性的,并且是不违背公平审判原则的,是能够保障当事人公正受审的权益的。关键在于民意不应当是在为政者“批示”之下作用于司法官,这样的民意已经不是民意了,而是命令了。
这个话题不得不再次牵扯出法官素质问题。中国法官总是很自信地认为自己不会受媒体舆论影响和左右,“最后的决定权在我手里”,无独有偶,美国法官也总是认为审判前的倾向性舆论并不会影响审判[47]。但是中美法官相似的态度背后,一定会有不同的依据。中国法官总是自信不受舆论影响,这或许是跟法官的职业经验、职业偏见或职业病有关,其实法官们压根就没有意识到自己实际上已经被舆论左右了。原因在于,我国缺乏“公平受审的权利”这一制度设计。这说明,如果在没有制度保障的前提下,也不能因为法官天然排斥媒体和舆论而轻信法官的自信。这也正说明了:法官的司法权是需要克制的,但这种克制不是通过形形色色的人盯人的政治性的监督,而是通过权利对权力、程序对权力、权力对权力的法律意义上的制约。
注释:
[1]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引自Marjorie Cohen & David Dow:《法庭上的照相机》,曾文亮、高忠义译,台湾商周出版社2002年版,第134页。
[2][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05页。
[3]孙笑侠:《公案及其背景—司法过程中民意的法社会学透视》,载《浙江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孙笑侠:《公案的民意、主题与信息对称》,载《中国法学》2010年第3期。
[4]何海波博士已对法律专家意见与公众意见的关系作了很好的分析,本文不再讨论这个问题。参见何海波:《公众意见与司法判决—对过去十余年若干轰动性案件的考察》,载《实质法治:寻求行政判决的合法性》,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
[5]参见前引[3]。
[6]“陪审团民主,它实在是伪民主的,因为它邀请或者至少是允许一个未经选举的匿名小组,它藐视立法机关通过的法律。每当发生这种情况,陪审团成为一个无法无天的机构,而这些陪审员渲染判决却永远不会被追究责任”。引自Jeffrey Abramson: We, the jury, The Jury System and the Ideal of Democracy. Harvard Press 2001. P4.
[7]韩蕾:《社会转型中的司法与民意》,载《理论观察》2009年第3期。
[8]我国1954年宪法第78条规定的是“人民法院独立审判,只服从法律”。现在看来,现行宪法的规定还不如54宪法那么直截了当、简洁明了。依其字面可知,法院独立审判,不服从法律之外的所有因素的影响,包括媒体和民众。依我的理解,司法权的独立性确实包括了这一层意思:司法权独立于民众和媒体。但是,司法权独立于民众和媒体的理由,不同于司法权独立于政府、团体和个人的理由。
[9]《群体性事件网上“一呼百万应”,基层干部不适应》,载《瞭望》新闻周刊,2009年6月,代群、郭奔胜、季明、黄豁。
[10]前引[9]。
[11]1849年2月,马克思在驳斥反动势力对《新莱茵报》的控告时指出:“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耳目,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同年12月15日,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出版启事》中,马克思、恩格斯又指出:“报纸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每日都能干预运动,能够成为运动的喉舌,能够反映出当前的整个局势,能够使人民和人民的日刊发生不断的、生动活泼的联系。”
[12]转引自滕彪:《镜城突围:司法与民意》,载《同舟共进》2008年第7期。
[13]参见前引[4]何海波书。
[14]前引[12]。
[15]2002年4月,刘涌被辽宁省铁岭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多项罪名一审判处死刑。民众拍手称快。但2003年8月,刘涌被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改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引起了舆论的一片哗然。民众群情激昂,强烈要求改判刘涌死刑立即执行,引起最高人民法院的高度重视。于是,在刘涌被改判死缓的两个月之后,最高人民法院于2003年12月22日在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刘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一案经再审后作出死刑判决。宣判后,辽宁省铁岭市中级人民法院遵照最高人民法院下达的执行死刑命令,当日对刘涌执行了死刑。
[16]参见前引[12]。
[17][美]沃塞曼:《美国政治基础》,陆震纶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49-151页。
[18]参见http://www. lawtime. cn/info/anli/mfjicheng/2008120953564. html。
[19]参见夏霖律师对崔英杰案一审的辩护词。http://xialinblog. blog. sohu. com/128965007. html。
[20]季卫东:《“馒头血案”引发的法治困境》,载《财经》总第154期。
[21]《深圳机场女工梁丽“捡,’黄金案余波未了》,记者吴俊,http://news. xinhuanet. com/legal/2009-09/29/content-12125448.htm.
[22]Jeffrey Abramson: We, the jury, The Jury System and the Ideal of Democracy, Harvard Press 2001. P4.
[23]1701年的《王位继承法》是最早确立“国王不得干预法律(法院)”的一部法律,正是从这里开始,确立了行政不得干涉司法的原则。在其后的300多年里,司法独立原则得到丰富和发展。从司法独立于国王,扩大到独立于一切行政机关、团体和个人。
[24][德]卡尔.斯密特:《宪法学说》,刘枫译,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4年版,第245页。
[25]奥托迈耶认为,司法权之中心点是确保人民权利,这是司法权的首要目的,所以要权力分立,司法独立。所以司法权必须完全由行政权脱离出来,并保持独立,任何国家权力不能干涉司法权的运行。参见陈新民:《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7页。
[26]孟德斯鸠划分国家活动的不同分支领域的目的是要用一种权力钳制另一种权力。参见前引[24]斯密特书,第247页。
[27]美国政治家汉密尔顿于1788年美国宪法起草中,根据国家权力的结构关系以及各自不同的强弱程度,认为“司法机关是分立的三权中最弱的一个”,所以需要让司法权独立。[美]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等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91-392页。
[28]例如,1982年国际律师协会第19届年会上通过的《司法独立最低标准》;1983年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的世界司法独立第一次会议一致通过了《司法独立世界宣言》;1985年在意大利米兰召开的第7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了《关于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后经联大1985年11月29日第40/32号决议及1985年2月13日第40/146号决议核可,成为一份国际性的法律文件。联合国经社理事会1989年5月24日第1989/60号决议又通过了《<关于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的有效执行程序》。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第6届亚太地区首席大法官会议特别重视司法独立问题,大会通过了《司法机关独立基本原则的声明》(又称“北京声明”)。
[29][德]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米健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101页。
[30]前引[29],第100页。
[31]1994年在国际法学家协会的司法与律师独立中心的召集之下,4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法学家和媒体代表,在西班牙的马德里相聚,签署了《关于媒体与司法独立关系的马德里准则》,该文件系统规范了表达自由与司法独立关系的规则。
[32]陈志武:《媒体言论的法律困境:关于新闻侵权诉讼的实证研究》,载怀效锋:《法院与媒体》,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66页。
[33]这一要求具有两个层次:“第一,具有道德责任心的人们强调按照他们自由的意志对生活中或政治中的善恶作出判断,或者对公正或信仰的真伪作出判断。当政府颁布命令,声明它不能放任它的公民听众危险而大逆不道的盅惑之言时,那么政府是在侮辱公民,并否认他们的道德责任。我们只有坚持——没有一个人—不管是政府还是大多数人—有权利认为我们不适合聆听和考虑某一观点从而取消我们的观点,从而维护我们作为独立个人的尊严。”参见德沃金:《自由的法》,刘丽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第282页以下。
[34]1985年3月27日,中央宣传部、中央政法委《关于当前报刊在法制宣传方面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通知》,1996年中央宣传部、全国人大常委办公厅、司法部和新闻出版总署下达的《关于新闻法制的意见》等。
[35]《对法庭绘图艺术家自由的限制》,载怀效锋:《法院与媒体》,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08页。
[36]1998年4月15日,当时新上任的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全国法院系统教育整顿工作会议上提出:“公开审理案件,除允许公众自由参加旁听外,逐步实现电视和广播对审判活动的现场直播,允许新闻机构以对法律自负其责的态度如实报道。”这在当时被社会各界视为人民法院落实公开审判原则,增强司法透明度的标志性转折。2003年1月27日肖扬在此间与新闻传媒负责人座谈时表示,人民法院将坚决依法惩罚那些侵害新闻机构和新闻记者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合法权益的违法犯罪行为,通过法律手段保护新闻单位和新闻记者的采访权和舆论监督权。 2006年9月12日,在全国法院新闻宣传工作会议上,这位首席大法官再次全面系统阐述了他对公开审判原则、司法与媒体关系的理念和认识。
[37]张震文:《最高法院如此规定有限制舆论监督之嫌》,载“红网”,http://hlj. rednet. cn/c/2009/12/24/1878149. htm.
[38]Marjorie Cohen & David Dow:《法庭上的照相机》,曾文亮、高忠义译,台湾商周出版社2002年版,第22页。
[39]美国宪法第六修正案规定“在所有刑事诉讼中,被告应享有获得及时与公开审判之权利”。
[40]Gannett Co v. DePasquale,443U. S. (1979)转引自Marjorie Cohen & David Dow:《法庭上的照相机》,曾文亮、高忠义译,台湾商周出版社2002年版,第66页。
[41]参见简海燕:《美国司法报道的法律限制》,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版,第100-101页。
[42]范伯格:《自由、权利和社会正义—现代社会哲学》,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5页。
[43]布兰德伍德:《公正审判与新闻自由》,载怀效锋:《法院与媒体》,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08页。
[44]前引[43],第118页。
[45]前引[43],第134至139页。
[46]前引[38],第230至232页。
[47]前引[43],第1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