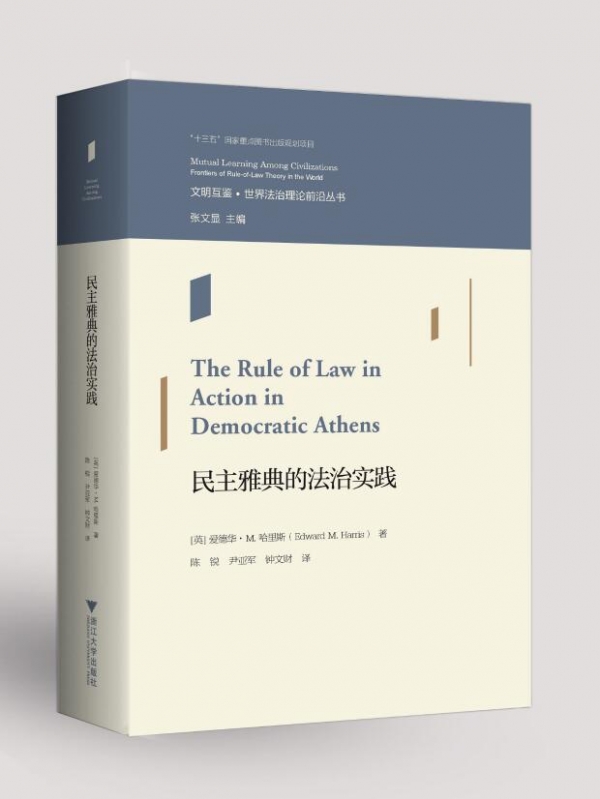《民主雅典的法治实践》
[英]爱德华•M.哈里斯(Edward M. Harris)著
陈锐 尹亚军 钟文财 译
ISBN 978-7-308-21507-7
出版时间 2021年7月
内容简介
《民主雅典的法治实践》一书重点考察雅典人在法庭裁决纠纷时如何实施和适用法律。最近的一些学术研究非常重视古希腊法律的实施和执行情况,然而,这些著作大多没有质疑以下几个有瑕疵的论断,如古雅典法律主要与程序有关;实施法律这一重要的工作掌握在普通公民手中;雅典人利用法庭,不是为了维护法律,而是为了解决个人之间的恩怨;雅典的法庭经常针对个案做出判决,很少关注法律的字面含义。作者借鉴现代法律理论,考察了雅典法律“开放性结构”的性质,并揭示雅典人对待法律的方式要比许多现代学者想象的更复杂,从而为该研究领域带来了相当大的突破。与此同时,本书探究了雅典法律体系的缺陷,分析其如何导致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失败。爱德华•哈里斯还通过重新审视现有的证据,对学者们长期持有的一些观念进行了必要的完善,并将雅典的司法活动置于广泛的政治和社会背景之中。
作译者简介
作者简介:
爱德华•M.哈里斯(Edward M. Harris),英国杜伦大学教授,主治古希腊史,发表了大量有关雅典政治、历史、法律和经济方面的著述,代表作有《埃斯基涅斯与雅典政治》(Aeschines and Athenian Politics,1995)、《古雅典的民主与法治》(Democracy and the Rule of Law in Classical Athens,2006)。此外,他还与R. W. 华莱士合编了《向帝国的过渡:公元前360-前146年的希腊—罗马历史随笔》(Transitions to Empire, Essays in Greco-Roman History 360-146 B.C., 1996),与勒尼•鲁宾斯坦合编了《古希腊的法律与法庭》(The Law and the Courts in Ancient Greece,2004)。
译者简介:
陈锐,安徽潜山人,哲学博士,重庆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研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出版学术著作(含译著)十余部,主编、参编教材四五本,主持刊物一两样。
尹亚军,现任教于西南财经大学法学院。重庆开县人,法学博士(西南政法大学),理论经济学博士后(深圳大学),“草街读书会”负责人。在《法制与社会发展》《法律科学》《北大法律评论》等刊物发表论文十余篇。
钟文财,广东梅县人,西南政法大学法学博士,英语专业八级,主研教育部课题一项,在《经济法论坛》《证券市场导报》发表论文多篇,其中一些被人大复印资料等转载。
引言(节选)
法治是雅典式民主制度最重要的文化遗产之一。公元前322年,在为殁于拉米亚(Lamia)的雅典将士举行葬礼时,希波雷德斯(Epitaphios 25)高呼:“为了人民的康乐,必须以法律之名而非某个人的威胁进行治理。自由人绝不能仅仅因为一鳞半爪的有罪证据而受到控告的威胁;我们公民的安全绝不能系于那些只知一味逢迎主人、中伤公民的人身上,而应建立在对法律的信任基础上。”(库珀译)在另一场葬礼演说中(这一演说可能未发表),吕西亚斯 (Lysias, 2.19)高度颂扬了雅典人的祖先,因为“他们认为,野生动物的典型特征是通过暴力手段在彼此间形成权力—服从关系,但人应通过法律界定彼此的权利,运用理性方式相互说服,并通过服从法治这一原则,在理性的指导下,实现上述两个目标”。修昔底德(2.37)认为,伯利克里 (Pericles)在公元前430年的葬礼演说中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在公共生活中,我们不得违反法律,因为我们随时准备服从执政的那些人及其法律,尤其是那些为扶助蒙冤者而制定的法律。”在雅典青年每年宣誓时使用的“埃菲比誓言”中,每个即将成年者都承诺遵守既定的法律,服从发布审慎命令的行政官员的领导,以及这些官员未来审慎制定的任何法律。在古希腊悲剧中,我们也能依稀发现法治的影子。当克瑞翁 (Creon)率军队入侵雅典领土并企图抓获俄狄浦斯 (Oedipus)时,提修斯 (Theseus)保护那些向其寻求庇护者,且提醒克瑞翁,他来到了一个践行正义的城邦,如果不依法办事,就什么都不能做(k’aneunomou)(S.OC 913-914)
雅典人发现,法治与“主权在民”(popular sovereignty)思想并不矛盾。实际上,他们甚至认为,这两种理念并行不悖。埃斯基涅斯 (3.6)断言,只要雅典人仍遵守法律,民主制度就依然安全。同一演说家还说道,当法庭容许自己被无关的指控分心时,法律就会被忽视,民主制度也会随之受到破坏(Aeschin.1.179.参见3.23;D.24.75-76)。在《诉提摩克拉底》(AgainstTimocrates)这一演说中,德摩斯梯尼(24.215-216)甚至宣称,雅典城邦的力量源于公民对法律的服从:
尽管您应该对那些可耻而邪恶的法律的制造者感到愤怒,但您更应对那些破坏法律者感到愤怒,无论这些法律是使我们的城邦变得虚弱,还是变得强大。并且,无论这些法律是什么,它们都是惩罚不法者、给践行正义者带来荣耀的东西。如果每个人都渴望做对社会有益之事,雄心勃勃地期待因此而获得荣耀与奖赏;并且,如果所有人都出于对可能施加于自身的损害和刑罚的恐惧而避免犯罪,那么,什么能阻碍我们的城邦变得更好? 难道雅典没有比任何希腊城邦更多的三列桨战舰、更多的重装步兵、更多的骑兵、更多的收入、更多的财产、更多的港口吗? 什么能保护和维持所有这些东西? 法律。当城邦服从法律时,所有这些资源都会为共同的利益服务。
伊索克拉底(15.79)曾自信满满地说,雅典的法律不仅为他们自己的城邦服务,而且为全人类带来了众多益处。
但雅典人对“法治”的理解是否与我们今天的理解一模一样? 或者说,我们能否将“法治”这一标签贴在雅典人身上? 我们能否将一种现代理念穿越时空地强加到古代的东西之上? 要回答这一问题,唯一的方法是确定现代学者所说的法治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并探寻民主制度下的雅典法律体系是否意图实现这些特征。尽管法律理论家和政治学家在法治的某些方面存在分歧,但论述法治的现代观点大多具有“法治”的某些基本特征。我们可以将那些试图定义“法治”这一术语的现代尝试区分为“弱的定义”(thin definitions)和“强的定义”(thick definitions)。“弱的定义”将“法治”的含义限定为:要求人们在司法和行政活动中,在适用已确定的规则时,保持前后一致;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建立官员问责制。“强的定义”要求更多,包括要求承认基本人权,等等。如今,大多数学者都采纳“强的定义”,尽管他们对哪一种人权应包含在这一定义中尚有不同的看法。
大多数学者都赞成的“法治”的首要特征是:法律应平等地适用于所有人。在有关法治基本原则的清单中,宾汉将这一原则纳了进来。他说:“除非我们能证明,由于(人与人之间)在客观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因此,区别对待是正当的;否则,大地上的法律应平等地适用于所有人。”按照戴雪(Dicey)的观点,“法治”原则要求:“没有人能凌驾于法律之上,无论人们的社会、经济或政治地位如何,他们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这一原则被吸纳进了1789年的法国《人权宣言》条款中(即,在权利方面,人人生而自由平等)。毫无疑问,雅典人相信这一原则,并在其法律中贯彻了这一原则。根据德摩斯梯尼(21.188)的说法,雅典人是通过法律而享有平等权的(参见D.21.67)。公元前403年颁布的法律明确地规定了这一原则:“除非同样的法律适用于所有雅典人,否则不允许将该法律适用于某个人。”尽管在公元前403年之前,这一原则没有被人们明确地表达出来,但它隐含在雅典的法律中。作为雅典最古老的几部法律之一,调整杀人罪的《德拉古法》(Draco Law )是以“如果任何人……”这样的表述开头的,并且,它没有在不同阶层的人之间做出区分。
一部可追溯到公元前485年或前484年的法律同样包含了几条以“如果任何人……”这一短语开头的条款(IGi34.l,第6-8、11-13、15-16行)。自公元前5世纪以来,还出现了许多其他的例子,可以作为公元前4世纪出现的众多例子的补充。这一原则不仅隐含在雅典的法律中,而且为当时的文学作品和演说辞所认可。公元前5世纪早期的一首著名饮酒歌,记载了哈莫迪斯(Harmodius)与亚里士多盖顿(Aristogeiton)杀死暴君的故事,人们讴歌他们的义举,称颂其使雅典人在法律面前保持了平等。在《葬礼演说》中,伯利克里夸耀:“依据雅典的法律,在与个人有关的争端中,所有人均享有平等权。”在欧里庇得斯(Euripdes)《乞援的妇女》(Suppliant Women,433-434、437;亦可参见D.51.11)中,雅典的统治者提修斯告诉来自底比斯的使者:“一旦法律被制定了出来,无论是无权者,还是富人,都享有平等的正义,处于正义一方、地位较低的人将战胜有权有势者。”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明显是一种雅典式理想,它不仅及于所有雅典公民,而且还延伸到了所有外邦人与外国人。在现实生活中,外邦人和外国人可能一直处在不利地位上,但在理论上,他们享有同等受法院保护的机会。
法治的第二个关键特征是:所有官员都是可问责的。古典时期的雅典确实如此:所有雅典官员必须无一例外地提交账目,其行为必须经得起司法审查(Aeschin.3.12-27)。每个官员都需要将账目提交给被称作公共会计师(logistai)的官员,由其核查账目,接受是否贪污、贿赂的审查。任何人都可以向那些被称为审计官(euthynoi)的官员检举、揭发(Arist.Ath.Pol.48.4-5)。米尔提阿德(Miltiades)在马拉松战役开始前和战后的短暂时间里曾两次受到审判,并在第二次审判时,被处以高额罚金。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初期,伯利克里虽拥有很大的权力和影响,但仍被罢免,且被判处了罚金(Th2.65)。正如我们在第九章将看到的,在接下来的一些年里,更多的将军和政治家受到了审判。在公元前4世纪时,将军和政治家被起诉、定罪的比例非常惊人。早在古风时代(theArchaicperiod),雅典人及其他希腊人就认识到,所有行政官员都应当可归责。早在公元前6世纪和前5世纪,希腊城邦的许多法律都包含了对那些不履行法律职责的官员进行处罚的内容。
法治的第三个基本特征是法律应当易于为所有人获取与理解。正如宾汉所言,“法律必须易于获取,且应尽可能地易于理解、清晰和可预测”。这包括几方面内容,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所有法规都应易于阅读和理解,且易于获得。古代的雅典人当然拥护这一原则。德摩斯梯尼(20.93)在《诉提摩克拉底》这一演说中说道,立法程序的目的是确保“相互冲突的法律被废止,以便在每个主题上都只有一部法律。这可以免于使那些不担任官职者产生困惑。与那些熟悉法律的人相比,后者明显处在不利地位。这一做法的目的是使法律条文对所有阅读者来说都具有相同的含义,且简单明了”。为使法律文本易于获取与理解,雅典人付出了诸多努力。德拉古和梭伦(Solon)的法律都写在转板(axones)与三角板(kyrbeis)上,它们可能由木头制成。直到公元前5世纪晚期,上述法律仍位居雅典人协商解决问题之要津。与特定领域有关的法律放置在管辖该领域的行政官员办公室旁边。即使这些官员分散在不同的办公室,人们也不难发现这些法律。在公元前4世纪,所有法律的副本都保存在自然女神庙(Metroon),任何人都可以随时查阅它们。在公元前403年之后,人们制定了新的立法程序,其中的一项要求是:所有提议制定新法律的提案副本必须陈列在阿哥拉(广场)的名年英雄(the Eponymous Heroes)纪念碑前(D.20.94;24.18)。一旦颁布,许多法律都会以公开的形式展示出来。在雅典的法律与法令中,经常包含一些有关如何公布法律的规定,比如,指示官员们将其刻在大的石柱上,放在每个人都能看见的显眼位置。例如,《尼高芬法》(The Law of Nicophon,公元前375年或前374年颁布)命令人们,将其刻在石柱上,其副本放在阿哥拉(广场)与比雷埃夫斯(Piraeus)银行业者的桌子中间,以及波塞冬石柱的前面(SEG 26:72,第44-47行)。另一部法律指示公民大会的秘书将其铭刻在石柱上,安放在雅典市中心的自然女神庙前。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这些石柱只是象征性的纪念碑,仅仅是为了纪念某一法律的颁布,而非供人们阅读,以便人们知晓其内容。由留存下来的几段法庭演说残篇可以看出,诉讼当事人在准备应诉时,经常援引这些法律。
我们在第三章考察司法誓言时会发现,雅典人试图确保“国家提供的审判程序是公正的”。为此,原告不仅需要将起诉书提交给被告,而且需要将准备提交法庭的所有证据都转给被告。法官需宣誓不受个人仇恨的影响,对诉讼当事人保持善意。原告和被告都将获得相等的发言时间。法庭由随机选出的法官组成,以确保公正。实际上,在一个即将于第六章考察的臭名昭著的案件中,被告没有获得足够的时间去应对针对他的指控,导致了雅典历史上最严重的司法不公,雅典人不久就后悔犯了这样一个错误。正如我们即将在第九章看到的,雅典的法律制度存在某些不足,这些不足主要表现为:那些旨在确保审判公正的措施带来了不可预见的后果。
现代法治观念的另一个原则是:如果某行为没有为法律所禁止,就不应受到惩罚。例如,《欧盟条约》第7条规定:“若按照国内法或国际法,某个行为在实施时不构成犯罪,则任何人不得因这样的行为(包括作为或不作为)而被认定为犯罪。”1789年的《人权宣言》第7条规定:“除法律规定的情况外,任何人不得被指控、逮捕或拘留。”第8条规定:“除非根据犯罪行为实施前已颁布且实施的或已合法适用的法律,否则任何人都不应受到处罚。”“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则为雅典的法律所承认(D.24.43)。
实际上,雅典的许多法律都载有这样一个条款,它指明,该法律只在“将来”(to loipon)或在某个日期之后才生效(D.24.43)。在雅典的法律中,还有这样一项规定:官员们不得使用不成文的法律(And.1.87)。这意味着,对于法无明文规定的不当行为,官员们不得随意处罚。所谓“法无明文规定”,是指(公元前5世纪时的)议事会、公民大会或立法专门小组(nomothetai)通过的法律中未包含(该行为),或(该行为)未记录在公开文件中。除非某人能明确地指出他人违反了雅典人民颁布的特定法律,否则不能控告他人(请参阅第三章)。毫无疑问,雅典人试图贯彻今人所理解的法治基本精神。
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应夸大古代与现代法治观念之间的相似性。现代法治观念通常建立在普遍人权基础上,可适用于所有种族与所有社会阶层,并同等地适用于男性和女性。对雅典人而言,法治主要是为雅典公民提供保障。例如,“反对仅针对某个个人而制定法律”这一规则要求:法律的颁布是为保障全体雅典人的利益(D.23.86)。
雅典的法律还保护妇女的权利。例如,禁止重伤他人(hybris)的法律明确将妇女纳入其规定之中(Aeschin.1.15)。一位演说家曾回忆起这样一个案子:一男子因实施了针对某一妇女的犯罪而被法院判处死刑(Din.1.23)。但总的来说,在雅典,妇女是无法到法庭提起诉讼或启动诉讼程序的,她们需要由丈夫或男性亲属代表其提起诉讼。若某位丈夫休妻,且拒绝归还妻子的嫁妆,或不愿意支付妻子的生活费,只有该女子的男性亲属才可提起诉讼。雅典的法律还严厉惩处那些试图奴役他人者,从而保障雅典公民和外邦人的自由(Arist.Ath.Pol.52.1),但这些保护措施并不能扩展到战俘身上。在希腊人中间,普遍流行这样的规则:基于征服权,战斗中被俘虏之人归胜利者所有(Pl.R.5.468a-b;Arist.Pol.1.6.1255a6-7;X.Cyr.7.5.73)。
雅典的法治观念与现代法治观念之间存在明显差异的另一个领域是酷刑的使用。几个世纪以来,世界上很多国家开始废除“以酷刑获取证据或作为惩罚”的做法。法国于1789年废除酷刑;同年,美国宪法第八修正案取缔了包括酷刑在内的“残忍和不人道的惩罚手段”。根据《欧洲公约》第3条的规定,“任何人不得遭受酷刑,或受到非人的、有辱人格的对待或处罚”。在所有这些情况下,保护人们免受酷刑的措施不仅适用于公民,而且适用于所有人;但相比之下,在民主的雅典,只有公民才可以受到免于酷刑的保护(And.1.43),奴隶和外国人仍可能受到酷刑的惩罚。
一些学者声称,雅典人对法律持一种“修辞性”态度,因为雅典的法官是借助诉讼当事人来理解法律的,后者可能会用差异巨大的方式解释法律。这一观点遭到了一些异议,首先,(雅典的)法律和法令是在所有公民都参加的公民大会上通过的。如前所述,新通过的法律副本放置在名年英雄雕像前,供所有人阅读。一些诉讼当事人告诉法官,他们最了解法律,因为法律是由他们制定的(D.42.18)。其次,即使诉讼当事人可以引用或解释法律,但在法庭上,通常都是由书记员而非诉讼当事人宣读法律和法令文本。法官从书记员那里听到的是真实的法律文本,而非其解释。 再次,(古雅典的)法官不像现代陪审员那样,一生只审理一两个案子。每一年,雅典都会选出6000名法官,任期12个月。在此期间,他们将审理数十个案子。与只能任职1年的雅典其他机构不同,雅典的法律并未禁止某个人连续多年担任法官。可以肯定,当时并没有对法官进行正式培训,因此,连续在法庭任职,将为他们提供有用的法律知识。这意味着,普通法官并不依靠诉讼当事人来了解法律。 最后,如果当事人对法律的含义存在相当多的异议,他们会希望对法律的含义进行广泛的讨论。但现存的演说辞所载的大多数案件主要涉及一些事实问题,这表明,在大多数案件中,原告和被告都暗含着赞同据以起诉的法律之含义。因此,我们没有理由认为,雅典人对法治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是“修辞性的”,并与现代的法治观念存在根本性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