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法学界有一种使用(也许是过度使用)“范式转型”(paradigm shift)的倾向,但其方式却与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的著名描述过程大相径庭。然而,在证据法领域,一种非常类似于库恩意义上的范式转型现象正在发生。它虽未达到从牛顿到爱因斯坦物理学或其他科学结构转型那样的规模,但对司法证明的最佳理解正在从概率主义向解释主义转型。几百年来,审判中的证明都被假定为概率性的。这种假定自从1968年约翰·卡普兰(John Kaplan)的开拓性文章发表以来,受到了学术界的持续关注与支持。这是一篇以概率来解释司法证明几乎所有方面的丰富文献,从相关性的基本性质到信息处理,再到关于事实的最终裁决。虽然概率主义很快就成为主流范式,但从乔纳森·科恩(L. Jonathan Cohen)对特定证明悖论(proof paradoxes)的论证开始,一些分析上的困难很早就被发现了(用库恩的话说,就是“异常”或“刺激物”)。罗纳德·艾伦(Ronald Allen)对此进行了拓展,他还论证了贝叶斯推理与审判的不相容,并提出了一种分析性替代方法。随之,主流范式的捍卫者炮制了大量文献,试图通过解释来消除那些异常现象,或者守护概率范式免受潜在的侵蚀影响(事实上,库恩在一个非常小的范围内关于科学范式转型的解释和预见正是如此)。在过去二十年里,这些异常现象已变得令人烦恼到不能再忽略它的程度,而与之竞争的解释性推论(相对似真性理论)范式的优势,已变得如此具有说服力而不容忽视。因此,该领域正在经历这种范式转型。
在此,我们对相对似真性理论以及概率范式的改进做了总结。正如库恩所指出的,当范式转变时并非所有人都赞同,总是有坚守者、反对者和异议者。最近有三篇主要论证相对似真性不足的论文发表。我们对其进行了分析,论证了他们的反对意见不是不合时宜就是徒劳的,从而奠定了相对似真性作为司法证明之最佳解释的基础。有趣的是,在我们所讨论的三种批评意见中,竟有两种实际上同意概率范式存在着不足(他们提供了替代方案)。第三种批评意见则承认,解释主义可能提供了一种关于司法证明的更佳进路,却试图鉴于一种特定的分析困难,复兴对证明责任的概率解释(即将证明责任适用于犯罪、民事诉求及辩护的单一因素而非当事人的完整案情,从而导致了合取难题的出现)。在分析我们的批评者所提出的替代性主张时,我们论证了他们的观点每一种都并不比相对似真性提供了更好的解释。
关键词:证据;证明;认识论;概率;最佳解释推论
引言
对审判中证明结构的“相对似真性”(relative plausibility)解释,是更为强劲的(robustly)概率解释之主要竞争对手。根据这两种解释,一般民事案件的主要目标是:在资源有限以及一些追求真相之外其他价值的证据规则的范围内,决定哪一方更可能胜诉。在刑事案件和一般民事案件中,这两种解释的主要目标也是一致的:出于政策的原因,使错误远离被告。这是通过提高证明标准来实现的,在刑事案件中必须达到“确信无疑”,在一般民事案件中要达到“清晰且令人信服的证据”。正是从这种一般意义上,一些作者把概率解释称作公认的证明进路。相对似真性与概率解释之间的分歧,并不在于法律制度在某种程度上是否试图规制错误,法律制度当然要规制错误。相反,它们之间的争议主要在于:其一,达成当事人案件的过程,对一项裁决的结论而言是足够充分的;其二,判决的性质。在民事案件中,“相对似真性”理论将这一过程解释为,旨在努力决定当事人各方证据和争议事项之各种解释相对似真性的推理过程。同样,在刑事案件中,类似的情况是决定检控方是否拥有似真的案情,如果有,被告是否也有似真的案情(即使没比控方的更似真)。相比之下,更为强劲的概率解释,将审判视为对一方当事人竞争性主张是否为真的问题进行一系列概率判断的更新过程。
换句话说,主要的分歧是经验性的:什么是司法证明的最佳解释?如果可能的话,解决这一分歧是很重要的,因为只有清楚地理解该制度实际在做什么,才能有效地对该过程进行评判。一旦清楚了该制度在做什么,人们就可以决定它是否以及如何能够被改进。然而,这里潜藏着一种复杂性,即美国法律制度本身极其复杂。大约有51个独立的“法律制度”在运作(实际上更多),每年要处理数百万的案件。此外,“美国法律制度”并不是一个为了单一目的而创建的静态实体,它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有机的、适应性的过程(或者,用更古老但也许更熟悉的哈耶克式术语来说,一个自然长成而非人造的制度)。这限制了捕获所有数据的具体简单理论或解释的能力,并且将会出现异常(outliers)。因此,目标不是要找到一种没有例外的单一解释,而是要试图尽可能地把握所研究对象的本质。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的主要目标是理解司法证明的一般性质。我们关注证明责任,以及证明责任作为观察法律制度的透镜是如何构建证明过程的。不过,证明责任仅仅是一个透镜而已。被观察到的是整个诉讼过程,其中包括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证明责任。这项任务是经验性的:什么是数据的最佳解释,“数据”在哪些地方体现了美国法律制度在审判中构建证明的方式?第二项任务是根据法律制度的目标,去考量经验真实是否具有应然的适当性。在司法证明的语境中,这些目标包括关于准确性和错误风险的特定政策目标。除了在实证基础上对比两种司法证明的解释,我们还比较了这两种解释与法律制度目标之间的契合度。
在以前的著作中,我们已论述了相对似真性比概率论提供了更好的实证性描述,也更契合于法律制度的规范性目标。许多学者近期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对我们的观点提出了具体的批评。在本文中,我们将对这些批评进行仔细审视,并解释为什么这些批评并没有削弱我们观点的基础。但我们不仅是回应其反对意见。在每一种情形下,这些作者都提出了关于证据性证明过程各方面的替代性解释。在捍卫我们观点之余,我们将对他们的每一种替代性观点进行批判,以阐明为什么这些观点都不能提出比相对似真性更好的描述性解释。此外,我们还指出了他们每一种进路都与法律规范性目标不一致的原因。
本文第一部分介绍了证明过程和过往学术争论的背景。我们概述了相关学说和政策考量,讨论了概率进路和我们的替代性解释进路(相对似真性),对概率进路的各种问题进行了检视,并阐明了我们的替代性进路为什么能够提供更好的解释。第二部分回应了大卫·施瓦兹和艾略特·索伯(David Schwartz & Elliott Sober)、戴尔·南斯(Dale Nance)、以及凯文·克莱蒙特(Kevin Clermont)在最近作品中提出的对相对似真性的反对意见。总体上,他们对我们的观点提出了六种反对意见——解释他们反对意见失败的原因,将使我们有机会进一步澄清和阐明我们的理论。尽管相对似真性提供了比传统概率进路更好的解释,但我们的批评者或许还有其他更好的替代性解释?我们在第三至第五部分考察(并驳斥)了这种可能性。在这些批评者中,施瓦兹和索伯最接近于传统的概率性进路,在第三部分,我们评价了他们试图捍卫概率性进路免受所谓的“合取难题”(conjunction problem)之努力。南斯和克莱蒙特各自提出了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传统概率进路的修正概率理论。我们在第四部分批评了南斯的理论,第五部分批评了克莱蒙特的理论。在考察了批评者的反对意见和替代性观点之后,我们回到开始的地方:相对似真性为现有的司法证明提供了最佳解释。
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概率性进路与解释性进路
这个部分首先论述了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的基本特征以及背后的政策。接着概述并对比了司法证明过程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进路,该过程的重点是但不限于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第一种进路即传统概率,将证明标准看作概率性阈值(thresholds)。第二种进路即相对似真性,将证明标准视为解释性阈值。我们描述了前者存在的一般问题,并阐明了为什么后者可以对证明过程提供更好的解释。
(一)证明责任与证明标准:原则与政策
证明责任为证据性证明过程提供了一个总体结构。对于犯罪的法律要件(legal elements)、民事诉因(civil causes of action)或者积极抗辩(affirmative defenses),一方当事人或另一方负有证明每一项要件的责任。通常情况下,控方和民事诉讼中的原告分别承担着对于犯罪和民事诉求的每一项要件的证明责任。对于大多数积极抗辩而言,通常由被告全部或部分地承担证明责任。审判中的证明责任由两个部分组成:举证责任(burden of production)和说服责任(burden of persuasion)。所谓举证责任,顾名思义,即要求负有责任的一方提出证据的责任。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需要多少证据才能满足举证责任?答案是:足以满足常人作出判断时的说服责任。说服责任由所适用的证明标准确定。
证明标准明确规定了负有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何时满足其责任。本质上,这些标准出于法律的目的要求一项争议事实何时被证明。在民事案件中,一般的标准是“优势证据”。在刑事案件中,更高的标准“确信无疑”适用于犯罪的各项要件。第三种中间性的证明标准“清晰且令人信服的证据”有时候适用于民事诉讼请求和积极抗辩。这些标准发挥着多种重要作用。最重要的是,在对审判中的争议事实进行证明而得出结论时,它们对审判事实认定者具有指导作用。此外,它们为证据的充分性评估——包括当事人起初是否有足够的证据继续进行审判,案件是否应在审判期间提交给陪审团,以及证据是否足以支持一项判决——提供了一系列指南。每一项决定都要求基于证据和证明标准对结果是否“合理”进行评估。
证明标准具有在面对不确定性时发挥事实争端解决的功能。几乎所有(实际上可能是所有)的司法事实认定,都是在不确定性情况下作出的。在现代诉讼中,这些标准基于两个相关的主要考虑因素,表达了如何解决不确定性问题的政策选择:准确性和在当事人之间的错误风险分配。通常认为,“优势证据”标准试图在当事人之间大致均等地分配错误风险,部分原因是两种类型的错误(积极错误与消极错误)被认为在社会成本方面是类似的。根据该标准,在证据势均力敌之时的“节点”上,法律旨在支持证据似乎支持的那一方,而反对负有说服责任的一方。据此,每一方都要承担这样的风险,即使是在那种他们应当获胜的案件中,证据似乎也可能会支持对方。此外,在特定假设下,优势证据标准也被认为最大限度地提高了整体准确性(或者最小化了错误总量)。这是因为该标准被认为有利于得出更可能为真的结果。最后,优势证据标准体现了一种民事对抗双方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
更高的证明标准(“确信无疑”和“清晰且令人信服的证据”)并不是试图将争议事项的错误风险均等化,而是试图将错误风险从一方(通常是被告)转移开。这种转移背后的明显政策是这样一种假定,即一种错误类型(积极错误)通常比另一种错误类型具有更高的社会成本。因此,更高的证明标准主要是为了减少一种错误类型(以牺牲另一种错误类型为代价),而不是试图使总体准确性最大化。因此,确信无疑的标准被认为需要比其他标准提供更多的证明,而清晰且令人信服的证据标准则要求介于优势证据与确信无疑之间的某种程度的证明。
(二)概率性进路
上文概述的特征与政策在抽象层面都获得了广泛的接受和普遍理解。它们为解释司法证明的任何尝试都提供了有益的开端。要确切解释这些特征是如何产生以及这些政策是如何实施的,这在法律制度的实际运行中已被证明是相当困难且有争议的任务。朝此方向迈出的首先且重要的理论步骤是,学者们试图依靠传统概率论来解释证据性证明过程的这些和其他特征,而概率一直都是试图理解司法证明各个方面的有重要影响的工具。然而,需要重点强调的是,各种概率方法提供了思考法律各方面问题的方式——它们既非法律特征本身所固有,也不必被纳入法律学说之中。
传统概率进路将证明标准定义为0~1区间的阈值。在此体系中,1代表确定为真,0代表确定为假,证明标准通常被解释如下:“优势证据”视为大于0.5的概率;“确信无疑”被视为0.9(或更高)的概率;“清晰且令人信服的证据”介于二者之间,通常概率在0.75左右。37对于每一有争议的法律要件,事实认定者都要评估该要件的可能性有多大(沿着0~1之间的数轴)。如果一个要件的概率超过了所适用的证明标准阈值,则可认为该要件获得了证明。当该要件的概率等于或低于该阈值时,则认为其没有得到证明。
在特定假设下,该进路将反映这些标准潜在的规范性政策选择。例如,优势证据标准作为一项受到约束的形式事项,证明一个争议性事实的概率要达到大于0.5(或大于50%),看似是在当事人之间大致均等地分配错误风险,以使错误的总量最小化。38相比之下,要求证明到一个更高的概率阈值——例如0.95的“确信无疑”或者0.75的“清晰且令人信服的证据”——则将更多的错误风险转移给负有证明责任的一方。
以这种方式使证明标准形式化,具有显而易见和重要的优势。例如,概率阈值为模糊不清的法律标准提供了清晰度和精确度(假设对这种阈值能够达成一致的话)。此外,概率框架还为衡量证据的相关性和证明力,为整合证据事项,基于新证据更新先前信念,以及评价结果的“合理性”,提供了形式化方法。
尽管有这些潜在的优势,但传统的概率性进路仍面临许多问题,从而使它难以在实证上难以被接受为对司法证明的普遍性解释。考虑到法律制度的政策目标,概率性进路在规范上也是不可取的(这并非否认概率性进路在解释或阐明证据或证明过程某些方面的能力)。总体来看,导致概率性进路不可取的问题可以分为四种主要类型。
第一,为了进行概率解释,必须将公理框架内的连贯数字分配给证据,以便将其与证明标准(假设为概率阈值,如高于0.5)相比较。尽管存在多种可以将概率概念化的方式,但有两种概率能够适用于法律证据。一种是依赖于客观数字的概率,如相对频率(relative frequencies)或者已知的统计分布(statistical distributions)。如果必要的数据都是已知的,那么,这种概率确实可以促进法律在准确性和错误风险方面的目标。但对于大多数证据而言,这些数据根本无法获得。即使对于能够获得数据的个别证据,也会遇到“参照组”(reference class)问题。鉴于这种“客观”方法的局限性,它根本不可能成功。当然,它与审判中的证明运行方式也完全不同。另一种概率依赖于“主观概率”(通常被描述为“确信”(credences)或者“信念程度”(degrees of belief))。这种方法也不能成为司法证明的一般性解释。无论是我们熟知的“先验主观概率”,还是创建用于更新先验概率的似然比(likelihood ratios)之“数字”,都可以是任何数字,在审判中要件事实(the facts of consequence)的证明过程中,它们并不需要受到证据质量或其证明力的任何形式约束。“主观概率”真的就是主观的。其提供了一种保持信念结构一致性的方法,但与促进结果的准确性没有必然关系。这样一种设想虽然对于实施某些解释而言是可行的(如果与客观数据同时更新的话),但其并没有促进证明过程在准确性和错误风险方面的基本目标。最后,主观概率进路与旨在衡量“证据充分性”的一系列法律措施(legal devices),以及基于证据和证明责任的特定陪审团结论是否合理,都是不一致的。
第二,概率进路(包括客观和主观的形式)与事实认定者运用证据进行加工和推理的方式是不一致的,后者是整体发生的,而非以该进路所预期的方式逐项进行。虽然该进路在理解证据方面具有一定的规范或教育价值,但显然是与实际的证据评价工作方式不一致的。这种不一致,对于任何此类旨在解释实际证明标准的实证性进路都是一个问题,因为它似乎要求或者暗示事实认定者以他们显然并不擅长的方式来评价证据。
第三,概率进路的假定一方面与法律原则不一致,另一方面也与给陪审团的指示不一致。为了使概率阈值能够实现其关于准确性和错误风险的目标,必须将它们应用于作为整体的案件(例如,原告的主张必须大于0.5才为真)。52然而,法律原理和陪审团指示通常规定将证明标准适用于单个要件,而非整个案件。因此,在一个包含两要件A和B的诉讼请求中,如果原告将每一项都证明到0.6,那么,根据法律其将胜诉。然而,倘若这两个要件是相互独立的,那么,原告诉求的概率是0.36,并没有大于0.5。这种矛盾已经成为所谓的“合取难题”(the conjunction problem),此问题将在后文进行更多的讨论。目前,重要的是要看到合取问题的两个要点。第一点是,法律将证明标准适用于诉讼请求、犯罪以及积极抗辩的各项要件。第二点是,当概率阈值(证明标准)被适用于单个要件而非它们的合取(整个诉讼请求)之时,概率进路将不再符合证明标准所预设的关于准确性和错误风险分配目标。鉴于第一点,第二点究竟如何理解,已经使证据法学者陷入争论。一种解释认为,法律犯了毁灭性的错误,并且如此惊人的错误在学理上应当被纠正。然而,另一种解释认为,这种矛盾可能揭示了概率阈值对于解释法律证明标准来说是一种糟糕的方法。至少,这些阈值不能解释当前标准是怎样运作的以及它们是如何与法律目标保持一致的。
第四,也是最后,将证明标准视为概率阈值的进路与证明过程和证明标准的目标均不一致。该阈值(如0.5)在以下意义上是不可比较的,即它们被表达为在概率轴上负有证明责任的当事人必须跨越的固定点,而没有考虑到对方当事人提出的替代性案情的概率。例如,假设原告必须证明其案件超过0.5,而被告只需要表明原告的案件只有0.5的可能性(或更低)。令人遗憾的是,这种对证明标准的解释与陪审团成员和法官评价证据的方式是不一致的,也与证明标准关于准确性和错误风险的目标不一致。
这里用一个形象化的例子来说明这些问题。抛开上面讨论的所有其他问题,假设原告提出的事实版本有0.4的可能性,而被告提出的替代性事实版本有0.2的可能性。原告的版本低于0.5的概率阈值,所以其将败诉。但是,原告的版本可能为真的概率,是被告替代性版本的两倍。据此,倘若目标是使得准确性最大化的话,原告应该胜诉。然而,其他0.4的可能性呢(?!),这是自然概率论者的回应。如果原告的版本只有0.4可能为真,那么,根据互补定理,原告版本可能为假的概率是0.6(因此支持被告而非原告,将使准确性最大化)。这就是该回应的问题所在。我们根本不知道,未知的概率空间是支持原告还是被告。此外,假设未知的0.4支持被告(就像传统概率解释所做的那样),那么,这就与在错误风险方面大致平等地对待当事人的目标不一致(相反,其强加了过多的风险给原告)。另一方面,拆分或者忽略该未知概率空间(等于一回事),与关于准确性和错误风险的既定目标是一致的。
综上所述,传统概率性进路不能作为司法证明的一般性解释,因为其(1)难以提供任何合理且可行的方式来量化证据并与概率化证明标准进行比较;(2)与法官和陪审团成员评价证据的方式不一致;(3)与关于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合取难题)的法律学说和陪审团指示不一致;(4)在方法上具有不可比性,与审判中的证明运作方式以及证明标准的潜在目标相冲突。
鉴于这些问题,概率性进路难以作为司法证明的一般性解释进路。然而,解释在性质上是比较性的。在我们完全放弃这种传统解释之前,还有更好的解释可以保留概率性进路所追求的这种有价值的社会功能呢?它在何处以及如何与传统进路形成对比?现在,让我们转向这些问题。
(三)解释性进路:相对似真性
相对似真性依靠解释性阈值来解释证明过程和证明标准。在描述该进路的具体内容之前,我们认为有必要强调这一理论不同于传统概率性进路的两个基本方面,以及两种进路相似的一个基本方面。不同点包括:(1)事实认定过程的核心标准(解释性的与概率性的),以及(2)证明过程是否被刻画为具有或不具有比较性。在解释性进路下,事实认定的核心任务,不是将概率附加到各项要件之上,而是决定证据和事件的潜在解释是否满足所适用的证明标准。此外,与概率性进路不同,解释性进路在本质上是比较性的——一种解释是否满足了证明标准,取决于支持每一方(而不仅是负有证明责任的当事方)的可能解释之强度。基本的相似之处在于,解释和概率两种进路都关注同一个目的:评估争议事实的似然率(likelihood)。然而,根据解释性进路,达到该目的的方式,是通过评价对比性解释的相对似真性,而不是试图将数字附加到信念上。
下面的讨论首先介绍解释性进路的具体内容,接着解释该进路如何避免前面讨论的概率性进路所面临的问题。其进一步表明,解释性进路是目前对司法证明的最佳实证性解释。
相对似真性进路不是将证明标准刻画为概率阈值(例如,0.5),而是基于解释阈值对证明标准进行相对似真性解释。证明过程涉及两个阶段:(1)证据和事件之潜在解释的产生,以及(2)根据所适用的证明标准对这些解释进行比较。通常,该过程取决于当事人获取的证据,以及提供他们认为支持其各自案件的最佳解释(或多种解释)。然而,事实认定者也开发和依赖那些由当事人提出的解释之外的解释。一方当事人的解释是否充分,将取解决于证明标准。解释阈值因标准的不同而不同,更高的标准要求更高的阈值。在“优势证据”标准之下,由事实认定者决定可获得的最佳解释支持原告还是被告。如果所获得的最佳解释包括了原告诉讼主张的所有法律要件,那么,其将支持原告;当其没有包括多项要件中的一项时,则将支持被告。许多一般性标准影响着解释的强度或质量。这些标准包括诸如一致性(consistency)、融贯性(coherence)、符合背景知识(fit with background knowledge)、简明性(simplicity)、没有漏洞(absence of gaps)以及需要作出不太可能的假设数量(the number of unlikely assumptions that need to be made)之类的考虑因素。例如,假设在一起非法入侵的民事案件中涉及两个争议要件:被告是否进入了原告的土地,以及被告是否故意为之。事实认定者将比较原告的解释(如,“被告故意进入原告所有的土地”)或者被告提出的解释(如,“原告误解了入侵者的身份”或“被告意外地进入了该土地”,或者两者皆有)是否更好地契合于庭审中提出的证据。
更高的证明标准对负有证明责任的一方要求更多。在刑事案件中,在“确信无疑”标准之下,控方在提出更好的解释(或者可获得的最佳解释)方面必须比辩方做得更多:在给定证据的情况下,只有当控方的解释(包括所有法律要件)是似真的,且不存在似真的辩方解释之时,事实认定者才能定罪。“清晰且令人信服的证据”标准要求一个介于优势证据与确信无疑标准之间的阈值。从解释性视角来看,这意味着原告的解释不仅必须要比被告的更好,而且对于决策者而言,也要比被告的显然更似真。
由相对似真性所设定(posited)的解释阈值,与证明标准的潜在目标是相匹配的。如上所述,这些目标包括有关准确性和错误风险分配的政策选择。根据优势证据标准,解释阈值在当事人之间大致平均地分配错误风险,因为每一方都承担着陪审团可能错误采纳对方解释的风险。此外,在一定的假设下,准确性将在一定程度上获得提高,因为更好的解释比不似真的解释更可能为真。同样,在更高的证明标准下,更高的阈值使得错误风险从不承担证明责任的一方转移开。据此,其表达了对于将一种错误类型(积极错误)而非另一种错误类型(消极错误)最小化的青睐。如同证明标准本身一样,这种转移在确信无疑的解释阈值中是最大化的,清晰且令人信服标准的阈值的则介于优势证据和确信无疑的阈值之间。
解释性进路也避免了前述概率性进路的每一个问题。再重申一下,这些问题是:(1)需要赋值以将证据和证明标准进行比较;(2)在概率论和事实认定者用证据进行实际评价与推理的方式之间缺乏一致性;(3)与法学原理和陪审团指示的不一致(合取难题);以及(4)与证明标准中潜在政策目标的不一致。我们将依次进行讨论。
首先,在解释性进路中,像在实际审判中那样,不需要对证据进行量化,也无需对满足法律要件的可能性赋值。相反,事实认定者会基于证据、他们的背景知识以及证明标准的解释阈值,来对可能的解释进行比较。这种溯因推理过程的可行性是解释性进路相对于概率性进路的明显优势,后者往往需要无法获得的信息来实现(或者必须依赖于主观信念)。此外,这种基于证据来预先对解释进行评价的标准,为评估证据的充分性或者具体事实认定结论(particular findings)合理性提供了手段。在主观概率性的证明观念之下,显然缺乏这些考量。
其次,经验性证据(empirical evidence)证实了事实认定者的推理以及律师呈现案件的方式更符合解释性进路,而不是概率性进路。陪审团成员通常试图构建符合证据的叙事(narratives),这与证明标准的解释性进路相契合。这种对证据评价的更为整体性的解释,与按概率对证据进行逐项处理从而导出关于每项要件之概率性结论的概率性进路,是格格不入的。
第三,解释性进路以一种直截了当的方式避免了合取悖论。再考虑一下一个包括两要件A和B的民事诉求。事实认定者不是逐项评估A和B并为它们分别赋值,而是评价原告的解释(包括或者包含A与B)是否比被告的解释(其将忽略A或B,或者AB)更好。基于解释阈值而选择一种解释,并对该解释进行评估,以确定其是否包括每一项要件。通过这种方式将案件与要件之间的关系概念化,改善了在概率概念下产生的“悖论”后果,它提供了符合证明标准潜在原理的法律解释。
第四也是最后,相对似真性的比较方面更符合证明标准的潜在政策。再假设一个例子,陪审团认定原告的解释(如,他由于年龄而被解雇)比被告的替代性解释(如,他由于表现不佳而被解雇)更有可能。进一步假设,按照概率解释来指示陪审团,陪审团成员必须给这些解释进行概率赋值。他们赋予原告的解释0.4、被告0.2的概率值。在概率进路下,原告将败诉,尽管其提供了一种更好(因而更可能)的解释。这种结果背离了准确性和平等分配错误风险的目标。这个问题产生于这样的假设,即如果原告的解释具有0.4的可能性,那么,被告不担责的概率则是0.6。相反,假设未知的0.4实际上是未知的,更符合这些规则的目标。尽管不需要量化解释,但解释性进路对未知的部分也做了类似假设。在解释性进路之下,双方当事人都不能事先从未知的可能性(unknown possibilities)中获益。因此,解释性进路不仅更符合真实实践,而且在解释这些规则方面也与其潜在目标一致。
这里用一个形象化的例子来说明这些问题。抛开上面讨论的所有其他问题,假设原告提出的事实版本有0.4的可能性,而被告提出的替代性事实版本有0.2的可能性。原告的版本低于0.5的概率阈值,所以其将败诉。但是,原告的版本可能为真的概率,是被告替代性版本的两倍。据此,倘若目标是使得准确性最大化的话,原告应该胜诉。然而,其他0.4的可能性呢(?!),这是自然概率论者的回应。如果原告的版本只有0.4可能为真,那么,根据互补定理,原告版本可能为假的概率是0.6(因此支持被告而非原告,将使准确性最大化)。这就是该回应的问题所在。我们根本不知道,未知的概率空间是支持原告还是被告。此外,假设未知的0.4支持被告(就像传统概率解释所做的那样),那么,这就与在错误风险方面大致平等地对待当事人的目标不一致(相反,其强加了过多的风险给原告)。另一方面,拆分或者忽略该未知概率空间(等于一回事),与关于准确性和错误风险的既定目标是一致的。
综上所述,传统概率性进路不能作为司法证明的一般性解释,因为其(1)难以提供任何合理且可行的方式来量化证据并与概率化证明标准进行比较;(2)与法官和陪审团成员评价证据的方式不一致;(3)与关于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合取难题)的法律学说和陪审团指示不一致;(4)在方法上具有不可比性,与审判中的证明运作方式以及证明标准的潜在目标相冲突。
鉴于这些问题,概率性进路难以作为司法证明的一般性解释进路。然而,解释在性质上是比较性的。在我们完全放弃这种传统解释之前,还有更好的解释可以保留概率性进路所追求的这种有价值的社会功能呢?它在何处以及如何与传统进路形成对比?现在,让我们转向这些问题。
(三)解释性进路:相对似真性
相对似真性依靠解释性阈值来解释证明过程和证明标准。在描述该进路的具体内容之前,我们认为有必要强调这一理论不同于传统概率性进路的两个基本方面,以及两种进路相似的一个基本方面。不同点包括:(1)事实认定过程的核心标准(解释性的与概率性的),以及(2)证明过程是否被刻画为具有或不具有比较性。在解释性进路下,事实认定的核心任务,不是将概率附加到各项要件之上,而是决定证据和事件的潜在解释是否满足所适用的证明标准。此外,与概率性进路不同,解释性进路在本质上是比较性的——一种解释是否满足了证明标准,取决于支持每一方(而不仅是负有证明责任的当事方)的可能解释之强度。68基本的相似之处在于,解释和概率两种进路都关注同一个目的:评估争议事实的似然率(likelihood)。然而,根据解释性进路,达到该目的的方式,是通过评价对比性解释的相对似真性,而不是试图将数字附加到信念上。
下面的讨论首先介绍解释性进路的具体内容,接着解释该进路如何避免前面讨论的概率性进路所面临的问题。其进一步表明,解释性进路是目前对司法证明的最佳实证性解释。
相对似真性进路不是将证明标准刻画为概率阈值(例如,0.5),而是基于解释阈值对证明标准进行相对似真性解释。证明过程涉及两个阶段:(1)证据和事件之潜在解释的产生,以及(2)根据所适用的证明标准对这些解释进行比较。通常,该过程取决于当事人获取的证据,以及提供他们认为支持其各自案件的最佳解释(或多种解释)。然而,事实认定者也开发和依赖那些由当事人提出的解释之外的解释。一方当事人的解释是否充分,将取解决于证明标准。解释阈值因标准的不同而不同,更高的标准要求更高的阈值。在“优势证据”标准之下,由事实认定者决定可获得的最佳解释支持原告还是被告。如果所获得的最佳解释包括了原告诉讼主张的所有法律要件,那么,其将支持原告;当其没有包括多项要件中的一项时,则将支持被告。许多一般性标准影响着解释的强度或质量。这些标准包括诸如一致性(consistency)、融贯性(coherence)、符合背景知识(fit with background knowledge)、简明性(simplicity)、没有漏洞(absence of gaps)以及需要作出不太可能的假设数量(the number of unlikely assumptions that need to be made)之类的考虑因素。例如,假设在一起非法入侵的民事案件中涉及两个争议要件:被告是否进入了原告的土地,以及被告是否故意为之。事实认定者将比较原告的解释(如,“被告故意进入原告所有的土地”)或者被告提出的解释(如,“原告误解了入侵者的身份”或“被告意外地进入了该土地”,或者两者皆有)是否更好地契合于庭审中提出的证据。
更高的证明标准对负有证明责任的一方要求更多。在刑事案件中,在“确信无疑”标准之下,控方在提出更好的解释(或者可获得的最佳解释)方面必须比辩方做得更多:在给定证据的情况下,只有当控方的解释(包括所有法律要件)是似真的,且不存在似真的辩方解释之时,事实认定者才能定罪。“清晰且令人信服的证据”标准要求一个介于优势证据与确信无疑标准之间的阈值。从解释性视角来看,这意味着原告的解释不仅必须要比被告的更好,而且对于决策者而言,也要比被告的显然更似真。
由相对似真性所设定(posited)的解释阈值,与证明标准的潜在目标是相匹配的。如上所述,这些目标包括有关准确性和错误风险分配的政策选择。根据优势证据标准,解释阈值在当事人之间大致平均地分配错误风险,因为每一方都承担着陪审团可能错误采纳对方解释的风险。此外,在一定的假设下,准确性将在一定程度上获得提高,因为更好的解释比不似真的解释更可能为真。同样,在更高的证明标准下,更高的阈值使得错误风险从不承担证明责任的一方转移开。据此,其表达了对于将一种错误类型(积极错误)而非另一种错误类型(消极错误)最小化的青睐。如同证明标准本身一样,这种转移在确信无疑的解释阈值中是最大化的,清晰且令人信服标准的阈值的则介于优势证据和确信无疑的阈值之间。
解释性进路也避免了前述概率性进路的每一个问题。再重申一下,这些问题是:(1)需要赋值以将证据和证明标准进行比较;(2)在概率论和事实认定者用证据进行实际评价与推理的方式之间缺乏一致性;(3)与法学原理和陪审团指示的不一致(合取难题);以及(4)与证明标准中潜在政策目标的不一致。我们将依次进行讨论。
首先,在解释性进路中,像在实际审判中那样,不需要对证据进行量化,也无需对满足法律要件的可能性赋值。相反,事实认定者会基于证据、他们的背景知识以及证明标准的解释阈值,来对可能的解释进行比较。这种溯因推理过程的可行性是解释性进路相对于概率性进路的明显优势,后者往往需要无法获得的信息来实现(或者必须依赖于主观信念)。此外,这种基于证据来预先对解释进行评价的标准,为评估证据的充分性或者具体事实认定结论(particular findings)合理性提供了手段。在主观概率性的证明观念之下,显然缺乏这些考量。
其次,经验性证据(empirical evidence)证实了事实认定者的推理以及律师呈现案件的方式更符合解释性进路,而不是概率性进路。陪审团成员通常试图构建符合证据的叙事(narratives),这与证明标准的解释性进路相契合。这种对证据评价的更为整体性的解释,与按概率对证据进行逐项处理从而导出关于每项要件之概率性结论的概率性进路,是格格不入的。
第三,解释性进路以一种直截了当的方式避免了合取悖论。再考虑一下一个包括两要件A和B的民事诉求。事实认定者不是逐项评估A和B并为它们分别赋值,而是评价原告的解释(包括或者包含A与B)是否比被告的解释(其将忽略A或B,或者AB)更好。基于解释阈值而选择一种解释,并对该解释进行评估,以确定其是否包括每一项要件。通过这种方式将案件与要件之间的关系概念化,改善了在概率概念下产生的“悖论”后果,它提供了符合证明标准潜在原理的法律解释。
第四也是最后,相对似真性的比较方面更符合证明标准的潜在政策。再假设一个例子,陪审团认定原告的解释(如,他由于年龄而被解雇)比被告的替代性解释(如,他由于表现不佳而被解雇)更有可能。进一步假设,按照概率解释来指示陪审团,陪审团成员必须给这些解释进行概率赋值。他们赋予原告的解释0.4、被告0.2的概率值。在概率进路下,原告将败诉,尽管其提供了一种更好(因而更可能)的解释。这种结果背离了准确性和平等分配错误风险的目标。这个问题产生于这样的假设,即如果原告的解释具有0.4的可能性,那么,被告不担责的概率则是0.6。相反,假设未知的0.4实际上是未知的,更符合这些规则的目标。尽管不需要量化解释,但解释性进路对未知的部分也做了类似假设。在解释性进路之下,双方当事人都不能事先从未知的可能性(unknown possibilities)中获益。因此,解释性进路不仅更符合真实实践,而且在解释这些规则方面也与其潜在目标一致。
在更普遍的层面上,尤其是在民事案件中,解释性进路也与诉讼的程序设置相协调。美国民事诉讼实践将收集和出示证据的任务分配给当事人,以适当激励他们在这些活动中投入最优的时间、精力和金钱,并且他们也是最了解相关事实的人。当事人决定提起诉讼的事项,调查方式以及在审判中作出何种解释。如果他们选择不对争议的某些方面提起诉讼,或者追逐一些相对不太可能却适当的假设,这也都取决于他们自己。正如全国的法院都经常强调的,当事人是其案件的主人。将证明标准以概率阈值来加以界定的任何其他方法,会使当事人用尽世上所有可能的方式去解决争议发生那一天的问题,或者更确切地说,如果做不到这些便对原告不利。这的确是一个艰难的任务。
总之,相对似真性从几个方面改善了证明的传统概率性进路。它并不要求将证据量化,而是为证据价值提供了一个更似真的概念;它符合事实认定的推理过程;它避免了合取难题;它为案件要件如何与整个案件相联系提供了一个似真性解释;并且,它的比较性质既符合审判中的实际证明实践,又符合证明标准的潜在政策。
当然,该理论也存在一些潜在的缺陷——解释性标准不具有概率阈值那样明显的清晰度和精确度,并且没有一种先验方式(priori way)来组合或排列各种解释性标准,以提供一个确定案件结果的一般性方法。对解释的评价将取决于在零售层面而非批发层面的个案细节,以及决策者的背景知识。但是,没有任何理论能够解释与司法证明一样复杂和动态的社会实践之所有方面,因此,如果相对似真性不能预测或解释一切,也就不足为奇了。不过总的来说,正如我们之前所坚持的,这一理论本身可以通过其相同的过程部署(deploys)来证明其自身的正当性:对于处于争议中的现象(即司法证明及其组成部分)而言,其是可获得的最佳解释。
相对似真性受到的批评
我们现在转向最近对相对似真性理论的三个批评。虽然每一种批评都承认传统概率性进路的一些问题,但他们对我们的基于解释性阈值的证明标准进路提出了一些挑战。此外,他们都提出了关于证明标准和法律相关方面的各自观点。在随后的部分,我们将以他们的替代性观点来讨论这些问题。在本部分中,我们关注的是他们对我们理论的具体反对意见。尽管这些反对意见并未削弱我们的理论,但讨论这些反对意见为何挫败,为进一步澄清和扩展我们的积极进路提供了机会。
我们根据主题组织了回应,首先关注由多个批评提出的重叠或相关的反对意见。接着,我们讨论他们各自提出的其他反对意见。这些反对意见涉及六个问题:似真性与概率之间的关系;不负证明责任的当事人义务;当事人对替代性或“析取性”解释的依赖;比优势证据标准更高的证明标准;合取难题;以及,事实认定者推论的性质。
(一)似真性与概率之间的关系
我们的批评者提出的第一个挑战,涉及解释的似真性与概率的关系。施瓦兹和索伯,以及南斯都认为这种关系是模糊的,亟需予以澄清。例如,施瓦兹和索伯宣称,我们的进路的具体内容是“模糊的”,“‘X可能为真’这种说法应该被改写成‘X是已知替代性解释中最佳的解释’”。南斯进一步指出:“帕尔多和艾伦并没有阐明或说明二者(似真性和概率)如何明显不同”。他一方面认为,如果一种解释的似真性意味着“讲述一个好故事”,而无论其多么不可能,那么,这根本不是一个好的法律证明标准。另一方面他又指出,我们所认同的解释性标准(一致性、融贯性、简明性等)“是评估认知概率(epistemic probability)的自然标准”。在这两种概率中,我们的观点更接近于第二种。下面将对此进行澄清。
按照我们的进路,法律事实认定确实旨在得出本质上具有概然性的结论。在此意义上,相对似真性与传统概率性进路都聚焦于同一个目的或目标之上。因此,我们的立场与上述南斯的第二种认知解释相似——推断哪一种解释更好,确实是基于证据推断出什么更有可能。也就是说,我们既不主张(1)将“更有可能”定义为“可获得的最佳解释”(如同施瓦兹和索伯所言),也不提倡(2)将基于解释性标准的推论转换成明确的概率判断(如南斯所言)。相反,我们依赖于如下事实,即审判中的推论具有回溯性(abductive)。关于什么是可能的判断,这取决于对解释之似真性的判断。换句话说,溯因是法律事实认定者达成概率性——即归纳性、非论证性(non-demonstrative)——结论的过程。这一过程本质上是比较的,在此意义上,特定解释的似真性(以及由此而得的可能性)将取决于可获得的替代性解释。总之,法律事实认定者通过评价和对比各种解释的似真性,而得出概然性结论。
法律中的溯因推理过程类似于科学、哲学以及日常生活等其他语境,在这些语境中,解释性考量指导着关于什么为真或者什么为可能的判断。哲学家蒂莫西·威廉姆森(Timothy Williamson)这样描述解释和概率的联系:
最佳解释推论不是根据潜在解释的概率,对它们(即这些潜在解释)直接进行排序。这并不会自动地使其与概率认识论(probabilistic epistemology)(例如贝叶斯认识论)相矛盾。当(通常会发生)概率(尤其是理论上的贝叶斯先验概率)难以评估时,最佳解释推论可能是一种很好的启发式(heuristic)方法。在此情形下,最佳解释推论可能是我们在实践中能够获得的最接近于概率认识论的方法。
威廉姆森侧重于理论上的解释,但他的描述也适用于司法证明中发生的许多事情。
然而,在法律语境中,推理过程并不总是关于选择最佳(因而最可能)可获得的替代性解释。解释之相对比较的具体内容,将取决于所适用的证明标准。提出可获得的最佳解释的原告,通过这种溯因过程提出了看起来是最有可能的解释。这就足以满足优势证据标准。并且,这一结果在一个又一个的案件中得以证实。它是充分的,并不是因为我们已经将“更有可能”定义为“更好的解释”。相反,解释性标准指导着关于可能性的推论与判断。因此,解释性进路并不是多余的,也不是概率性进路的同义词,尽管两者都旨在得出概然性结论。
(二)比较性证明与被告义务
第二个挑战:我们的批评者声称,我们的进路与法律不一致,因为其要求被告(或者更确切地说,不承担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替代性解释。例如,施瓦兹和索伯认为,证明标准的解释性进路需要面对的一项“困难”,是“即使被告没有提出积极的相反解释,原告也不能自动胜诉”这一法律规则。同样地,克莱蒙特也认为,我们的进路“通过强迫不负证明责任的一方,或者至少强加一种实际义务来选择和制定与之竞争性的真相版本,从而背离了法律。”他解释道,法律原则“允许保持沉默的被告仍然可以获胜”。这些观点有一定道理,但与阐明问题相比,它们更具误导性。澄清为什么会这样,也有助于揭示为何这一挑战所引起的关注并不影响我们的进路。
有关证明责任的标准化陪审团指示和法律原则表明,不负证明责任的当事人(通常是民事和刑事被告)不要求提供替代性解释。确实如此。然而,我们之前已经表明,这种说法具有严重的误导性。首先,审判以无数种方式组织,以便比较原告和被告的解释。有关证明责任的指示是不合时宜的(the odd man out)。
但更重要的是,“法律”说什么并不重要,因为除了做这种比较之外,别无选择。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提出的诉讼主张之可信性,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替代性解释是什么。如果事实认定者得出结论认为,原告的案件已被否决,那就可以确定,除原告所指控的以外还发生了其他事情。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当然,在某些情况下,原告的指控不可能是真实的,但这也是由于原告案件的某些要件不可能发生——一定是存在其他情况,而事实认定者必须拥有多个似真的备选解释,来得出这样的结论。
因此,从表面上看这是对的,作为一个正式事项,民事或刑事案件中的被告确实都不必提供替代性解释,或者根本无需提供任何解释。但事实上,他们几乎总是这样做。原因很明显:如果只有一种对证据的似真解释,公正和理性的人将会得出结论认为:这是真的。换句话说,那些“保持沉默”(stand mute)的被告——法律通常允许他们这样做——将败诉。这就是为什么诉讼律师不首先讨论“否定”对方的“案情”,而是表明他们(自己)关于该事实的版本才是真实的。类似的考量甚至适用于刑事案件。当被告对控方的解释进行质疑时,由于证据提供了替代性解释,所以控方的解释可能是不似真、不可能或“毫无意义”的。另一方面,当面对一个强有力的指控案件时,被告可以保持沉默并可能被定罪,或者,他们将努力提出似真的替代性解释。
但是,我们的批评者声称,在许多案件中,被告(民事或刑事)的辩护是基于“发生了其他事情”,而非提供任何具体的替代性解释。他们指出,这些是我们理论的反例。我们对此并不认可。这些情况确实存在,但作为回应,重要的是认识到以下三点:其一,这种在审判中的一般性论点——即“发生了其他事情”并未具体说明发生了什么——正如施瓦兹和索伯所主张的,并非证明责任的特征。承担证明责任的一方有时也可通过这种一般性论点获得成功——例如,在事实不言自明(res ipsa loquitur)的案件中,原告未能确定具体的原因,却可以通过证明“被告的过失行为导致自我损害”而胜诉。因此,一种理论必定能够解释而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在审判中这些论点的存在是证明责任之必要特征,这是错误的。其二,这种在审判中“发生了其他事情”的论点(无论是否由承担或者不承担证明责任的当事人作出)的案件数量是有限的,它们是例外而非诉讼的常态。再次需要牢记的是,这里所考虑的是一个庞大的、不断蔓延的系统,其有时会变得难以控制。其三,即使当被告没有提出一个具体替代性解释时,事实认定者仍会通过考虑可能的替代解释(基于他们自己的知识库)来评价原告或控方的解释。例如,与最后这一点相关的是,克莱蒙特教授注意到,“在审判过程中,可能会自然而然地形成一种对负有证明责任一方的真相版本乃是虚假的信念。”当然有可能,因为原告的证据确实可能表明,除了他或她所声称的之外,还有其他事情发生。除了得出发生了其他事情的结论外,对原告版本的“否定”信念又是如何产生的呢?
总体而言,法律没有正式要求,不负证明责任的当事人去承担超越现行法律规定之外的任何义务,这充其量是出于对正式法律结构与人们思维方式之间差异的好奇。被告可以选择“保持沉默”,根据法律原则,他们经常被允许这样做,然而这将给他们带来危险。鉴于所争议的证据和事实的性质,有时不提出关于事件的具体版本而是依赖于更一般性的断言,将是对当事人有利的。他们能否成功地这样做,将取决于有效实施的实体法,而不一定要遵循证明责任。最后,无论当事人双方是否都提供了具体的解释,事实认定者(作为人类推理者)都会评价在其知识背景下所获得的任何解释,以及该知识所暗示的其他可能解释。
(三)替代性或者析取性解释
前一个挑战涉及被告提供替代性解释的义务。我们的批评者提出的第三个相关挑战是,事实认定者是否会考虑当事人没有提出的替代性解释,以及当事人是否会提供“析取性”(disjunctive)解释(或将两种或更多可能性结合起来的解释)。批评者认为替代性的或聚合性的(aggregated)解释使我们的理论呈现出这样一种困境:要么(1)我们不允许它们,这既违反了现行法律,也会导致更多事实错误这种不良后果;要么(2)我们允许它们,这将导致我们的理论与传统概率观“趋同”进而“崩塌”。
我们的回应主要集中在这一所谓困境的第二个方面。在之前的文章中,我们已经论证了司法证明允许替代性解释和析取性解释。133在这里,我们解释为什么与我们的批评者所主张的相反,这些解释不会削弱我们的理论。不过,在转向该困境的第二方面的具体内容之前,讨论析取性解释将有助于澄清关于第一方面的一些细节,同时也与第二方面相关。
相对似真性指出,事实认定者比较及评价关于证据的竞争性解释。一些批评者将这一比较过程的要求解读为:(1)每一方必须选择且只能选择事实的一种版本来与证据相比较,以及(2)事实认定者必须只考虑这两种解释。然而,在我们的进路中并没有要求对事实认定过程进行这些限制。我们赞同,事实认定者可以自由地考虑和推断当事人没有提出的可能性,而且,我们意识到,法律有时候也允许当事人通过提出替代的可能性进行“析取”。后者可能发生在给出两种不同可能性之时,也有可能发生在被告援引支持无责任的全部可能性范围之时。法律是否允许当事人这样做,以及这样做是否有意义,将取决于案件的具体内容。不过,一般而言,当事人在选择如何出示他们的案件方面有很大的空间——这些选择之一将涉及他们希望援引多大的可能性或概率空间来支持自己的案件。这可能涉及一个故事,一个由两种(或更多)可能性组成的析取性解释,或支持他们案件的整个概率范围。我们的进路符合这种情形,比较过程是在各方如何选择对比其案件的背景下进行的。
虽然我们承认析取性解释,它也有助于澄清我们的批评者为什么认为两种解释的一个相对比较,将“增加错误裁决的风险”并“导致原告比通常情况下更常获得赔偿”。再回到我们的例子,事实认定者得出结论,认为原告的解释是0.4的可能性,被告的解释是0.2的可能性。正如我们上面所解释的,当余下的0.4是未知时,比较性进路(原告胜诉)更符合准确性和平等分配错误风险的目标。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批评是基于这样的假设,即所有未知的可能性都应该支持不承担证明责任的一方,这是与优势证据规则的目标相矛盾的。然而,更可能的情况是,我们的批评者认为剩余的0.4也是支持被告的第三种可能性。如果是这样,并假设法律允许这种析取的话,那么我们赞同,被告不应被限制去选取这一个或者那一个;相反,被告应该胜诉,因为与原告的版本相比,这种析取的可能性更大。
做了这些澄清之后,我们现在直接转向所提困境的第二方面。确切地说,我们的批评者为什么认为,接受析取性解释会导致我们的理论崩塌?南斯认为,之所以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支持每一方的“最似真解释”将总是支持每一方的“所有可能故事的析取”。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该理论就变成与决策理论标准相同了”。施瓦兹和索伯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认为析取解释导致了我们的进路与证明标准的传统概率性进路趋同。按照批评者的说法,我们的理论只有在“要求对事实认定者的故事聚合作出进一步限制”的情况下,才能避免崩溃。出于两个原因,我们不认同这些批评。
其一,批评者们依赖于该真实(且明显)的暗示,即如果我们允许对整个概率空间进行析取,那么,我们将像传统概率进路那样,总是在填充该空间。然而,这种暗示并没有导致解释性进路显得多余。需要明确的是,我们拒绝原告的解释必须占据一半以上可能的概率空间这一假设,如果认真考虑的话,这将要求原告证明,该空间的一半以上已经支持自己。但即使我们承认这一假设,解释性进路在几个重要方面也仍然不同于传统概率性进路。例如,仍然是解释性标准指导推论,解释性考量为证明标准提供阈值,而非概率性标准和阈值。即使前者最终涉及概率性结论,情况也是如此。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解释性进路提供了一种更好的司法证明进路,即使双方当事人把所有的可能性都摆到桌上。
其二,也是更重要的,并不是我们的理论需要为聚合解释(aggregating explanations)设置限制原则。法律、当事人以及事实认定者已经这样做了。受法律的某些限制,双方当事人在决定援引多大概率空间(以及具体性或一般性的程度上)和如何最好地将他们自己的案件与对手的案件进行对比方面,都留有余地。
需要明确的是,我们看到了我们的批评者们正在试图表达的观点:当然,支持每一方的最可能的解释,将是支持那一方的所有可能解释的析取(其将至少与任何单一析取项或子集一样可能)。但是,这里有另一个例子,在该例子中传统概率性进路的形式与审判实践是分离的。在审判中,援引可能性的全部范围往往不利于当事人。考虑一下民事被告可能掌握争议事件中实际发生信息的任何案件。当面对特定原告关于被告担责的解释时,对被告来说,给出表明其无责任的替代性版本,比做如下争辩将很可能更有说服力:“不是我;或者,虽然是我,但这是一个意外;或者,我确实故意这样做了,却是别人造成了该损害。”或者设想在一起谋杀案中,控方已经提供了有罪的证据解释。据推测,我们的批评者大概会认为,被告可以带着电话本上法庭说:“可能发生了别的事情”,而这将摧毁相对似真性解释。在第一点上他们是对的,但关于第二点却是错误的。被告大概可能这样做。令人诧异的是,被告们却都没有这么做。正如我们当中一人所说,当事人都是模糊性的丢弃者,而非创造者。他们并未选择对“整个概率空间”起诉,因为这样做几乎总是给事实认定者带来法庭灾难。
因此,在比较不同的解释时,我们不赞同说,一方当事人所能提供的最似真解释,总是可能的析取项之全部范围。解释性进路再一次比概率性进路更契合于实践。后者认为,并不是一直都争论析取项的全部范围,因为它完全没有意义。相比之下,解释性进路与当事人在如何定义和对比其案件方面所作出的选择相适应。它还适应于以下概率:事实认定者可能会考虑各方当事人未提出(或者选择不提出)的替代性解释;概率性进路则认为他们应该总是为每一方考虑所有可能解释。
总而言之,在没有降低传统概率性进路的情况下,我们的理论解释了替代性和析取性解释,也更加契合于这些解释在审判中产生以及使用的方式。
(四)更高的证明标准
第四个挑战关注除优势证据标准之外的证明标准——“确信无疑”和“清晰且令人信服的证据”。尽管我们的批评者承认,在优势证据标准与解释比较之间有一种自然的契合,但他们主张,我们的理论不能解释更高(或更低)的证明标准。克莱蒙特认为,解释的“依次比较”,“无法轻易解释比优势证据标准更高或更低的证明标准”,因为,所有其他标准“很难以比较的方式进行表达”。南斯在其批评中更进一步宣称,我们关于这些标准的解释,“对于非闭合性地进一步澄清这些标准的意义或理由,于事无补”。此外,他坚持认为,确信无疑标准的解释性进路,“完全放弃了对比较性的强调”,并且“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具有比较性”。
这些批评都偏离了目标。在澄清我们的理论如何以一种非闭合方式解释这些标准之前,我们首先关注所有试图为这些标准赋予内容的理论所面临的一项困难:即缺乏清晰的标准——它们是不明确的、模糊的,并且经常存在不确定的应用。即使是在那些主张和假设这些标准表达了概率阈值的人之中,对于概率应当如何概念化、数字应该是什么以及标准应当如何适用于个案,也存在相当大的差异。的确,据我们所知,在批评了相对似真性理论在这方面的模糊性之后,没有一个批评者对什么是清晰且令人信服的证据和确信无疑,提出自己的精确解释。鉴于这些标准缺乏明确性,如果对这些标准的描述性或解释性进路能够消除在其含义或适用方面的所有不确定性,那确实是令人惊讶的。据此,我们不认为,不能解决围绕这些标准的所有不确定性,就是我们理论(或者任何其他理论,包括概率论)的失败。
这种对我们关于更高证明标准理论的特殊挑战,是基于两个假设,但它们都是错误的:第一,我们对证明标准的解释是“闭合的”;第二,更高的证明标准不是也不能用“比较性”术语来表达。我们分别进行说明。
我们的理论从解释性阈值的视角来解释证明标准。在优势证据标准之下,解释性阈值是直接进行比较的:负有证明责任的一方,必须基于证据和事实认定者的认知能力,对证据和事件提出比其他替代性解释更好的解释。更高的证明标准对负有证明责任的一方要求更多,因此,在我们的理论中需要提高解释性阈值,以满足更高标准的要求。当存在有罪的似真解释,且没有无罪的似真解释时,确信无疑标准就得到了满足。根据此观念,定罪所要求的证明标准,比优势证据标准要高得多。即使控方的解释比被告的更好,被告也可能胜诉——任何无罪的似真解释(未被证明或消除的解释)对于提出一个合理怀疑而言都是足够的。同样,即使辩护性解释没有被提出(或者由事实认定者所构建),如果事实认定者得出结论认为控方的解释不具有似真性,那么,该标准也没有得到满足(无论其是否比被告的解释更好,也可能根本没有被告的好)。以这种方式提高解释阈值,符合该标准将错误风险从刑事被告身上转移开来的目标。
类似的考虑,也适用于众所周知的模糊性标准——“清晰且令人信服的证据”。该标准适用于某些类型的民事案件(以及刑事案件中的积极抗辩),通常被假定为是介于优势标准和确信无疑之间的中间标准。据此,负有证明责任的当事人不需要消除任何合理怀疑,但他们必须比证明这些要件更有可能为真做得更多。因此,这一中间标准反映了关于准确性和错误风险的中间立场。然而,对于该标准在这些要求之间的确切位置,还不是很清楚。我们过去(和现在)也没有打算为这一标准应该是什么提供一个精确的固定位置,正如上面所提到的,其他人也没有这样做——相反,我们已经尝试用解释性术语来解释现有的标准。我们的理论提供了一种介于优势证据标准和确信无疑之间的解释阈值。一方面,为了满足该标准,当事人不必有唯一似真的解释(不像确信无疑那样);另一方面,当事人必须比仅仅提供可获得的最佳解释做得更多。当事人不仅必须提供比替代性解释更好的解释,而且要更有说服力,无论在何种程度上,都要使其“清晰且令人信服”。在实践中,这通常意味着,只要事实认定者决定哪种解释更好的问题只是一种“侥幸的胜出”(close call)之时,被告都应当胜诉(即使事实认定者认为原告的解释略微更好一些)。
解释性进路并不是“闭合”的。根据我们的理解,如果一种进路没有提供除在标准本身的描述中已包含内容之外的新内容或要求,那么,其就是闭合的。标准本身并未提到或涉及解释或解释性标准。在以解释阈值解释标准时,我们为澄清这些标准所要求的是什么,它们怎样符合该过程(包括推论过程和评估证明力)的其他方面,以及它们怎样符合规则的政策目标,提供了额外内容。换句话说,将这些标准描述为解释阈值,并不是简单地对其进行重述。当然,解释阈值没有为这些标准提供“量化”或“比率”,但是,这并没有使其变得闭合。我们的观点是,承认满足证明标准的标准是解释性的,并且承认,每种标准都要求不同的解释阈值,从而使这些标准本身变得(非闭合的)清晰和容易理解了。
现在转向该挑战的第二个方面,批评者还主张我们的进路不再具有比较性,因为确信无疑和清晰且令人信服的标准不能以比较术语表达。我们对这个批评感到困惑。其中一些困惑涉及模糊性,即在这种语境下“比较”意味着什么?如果“比较”是指,只有当一种解释比其他替代性解释更好时——或者,不负证明责任的当事人必须提供至少与其对手一样好的替代性解释时——该标准才能被满足,那么,是的,我们赞同它们在这种意义上并不具有“比较性”。这是优势证据标准。正如我们已经解释过的,除了直截了当的比较,更高的标准(以及它们所要求的阈值)还有更多的内容。然而,在另一种意义上,更高的标准仍然是“比较性的”。即在确定阈值是否得到满足的意义上,它们是比较性的,因为其将包括考虑和比较每一方可能的替代性解释。换句话说,直到事实认定者已将一方的解释与替代性解释进行了比较之后,才能认定解释阈值已经被满足。确实,在刑事案件中,如果检控方没有提供足够强有力的案情,事情就可能永远不会发展到这一阶段。但是,在确信无疑标准被满足之前,必须与可能的辩护性解释进行比较(事实认定者必须审查是否存在任何无罪的似真解释,因为在这些案件中应该宣判无罪)。同样,在运用清晰且令人信服标准的案件中,如果没有将其与替代性解释进行比较,你就不能确定原告的解释是否足够好。按照解释阈值来阐明更高的标准,就要求解释必须基于可能的替代性解释进行评价——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是比较性的,但是,解释阈值对这些标准提出的要求,比仅仅优于替代性解释要多。
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这种批评表达了一种对标签化而非潜在推理的不满。的确,我们已经将所有标准集中在“相对似真性”的标签之下,该标签更直接地映射到了优势证据标准上,但是,我们也清楚地说明了解释性进路如何处理其他标准。
(五)解释与合取难题
施瓦兹和索伯提出第五项挑战。正如在第一部分所讨论的那样,事实上证明标准通常适用于单个要件而不是整个案件,这给传统概率性进路带来了概念上的困难。由于法律似乎忽视了合并各个要件的形式后果,并且似乎容忍背离证明标准目标的结果,这种所谓的“合取难题”便产生了。然而,我们的进路则避免了合取难题,因为在对解释进行评价时,证明标准适用于整个案件并分配给双方当事人。接着,这些要件在确定所选择的解释是否包含形式要件时发挥着作用。
并非如此,施瓦兹和索伯就对此表示反对。他们主张,即使我们避开了证明标准的形式概率框架,我们的进路也面临着同样的合取难题。他们认为,如果原告必须在“每一要件”上获胜,那么,“合取难题就会重演”。为什么这一难题会重演呢?他们声称这是因为:
所有解释性理论告诉我们,事实认定者履行这两项任务——确定最可能的整体性主张,以及对每一要件的最可能的解释——无需实际进行乘法运算。
他们假设,因为我们的理论“要求对所有要件分别进行审视,以确定原告在每一要件上都有最佳解释”,以及当陪审团成员“依次裁决这些要件时”,可能结果会发现原告对每一要件都有最佳解释,但对整个案件却没有最佳解释,这与原来的合取难题情况相同。他们在概括这一特定批评的结论时指出,如果我们对每一要件和整个诉讼主张都适用解释性标准,那么,我们的理论将与他们所偏爱的证明要求趋于一致(南斯之前提出的观点)。
所有这些批评都是基于对我们理论的误读。施瓦兹和索伯的批评所做的错误假设是,我们的理论“需要分别考察各项要件,以确定原告对每一要件都有最佳解释。”他们假设,这就是“包含”或“具体化”各项形式要件的解释之含义。然而,根据我们的进路,竞争性解释的评价是基于证明标准的适用,而非逐项要件进行。它是在整个诉讼主张的层面进行的——一旦选择了所选取的解释,则将其与形式要件进行比较,以确定其是否包含在该解释之中,或者是否适用于该解释。施瓦兹和索伯认为,将证明标准适用于每一项要件将再次产生合取难题,这一观点是正确的——这不仅适用于传统的概率性进路,也适用于其他理论进路。不过,这并不是我们的理论。
(六)解释与推论过程
最后,且与前面的挑战有关,克莱蒙特基于事实认定者是在“整体上”评价竞争性解释而非逐个要件地对证据和推理进行评价,提出了第六项挑战。他主张,我们的理论与这种推论过程之间的关系,给我们的理论带来了两个潜在问题。其一,这似乎与告诉陪审团成员要逐个要件进行评价这一陪审团指示相矛盾。其二,这意味着该理论带有“包袱” (baggage),因为其要求某种类型的整体主义进路来处理证据(例如故事模型)。我们依次进行讨论。
首先,根据我们的进路,我们已经解释了关于要件的陪审团指示如何适用于解释(它们在解释的选择之后起作用)。在这种解释中,并不存在矛盾。然而,更重要的是,无论陪审团指示在这一点上说了什么,显而易见的是,事实认定者实际上是在整体上进行操作的——这是信息处理的方式。再次强调一下,关于证明责任的陪审团指示,只是需要解释的一部分。除了这些指示之外,司法过程系统地对民事和刑事案件的当事人施加了比较性的过程。我们认为,符合这一过程,对任何司法证明理论来说都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一项对我们的理论符合这一过程而传统概率理论却与之不符的检验。如果陪审团指示的某些方面似乎与这一事实不一致,那么,正如我们上面所论述的,陪审团指示的这些方面就是反常的。
其次,我们不赞同将符合证据的实际处理方式视为“包袱”。考虑到我们特定的理论目标,至少对解释现行的司法证明过程是这样的。我们的进路是一种“自然化”(naturalized)方法——将当前关于人类认知的事实与局限性纳入考虑之中。结果可能是,其他理论可以更好地解释其他可能世界的证明标准,例如,人类(或其他类型的决策者)以不同的方式进行推理,以不同的方式进行审判,或者无穷尽的其他事情都是不同的。但是,鉴于我们所关注的事项,我们认为,因其符合证据处理的主流实证进路,我们的进路有优势而非缺憾。
然而,在最后一点上,我们再次强调彭宁顿和黑斯蒂的“故事模型”与相对似真性之间的区别。克莱蒙特指出,我们的理论在某种程度上与故事模型存在联系。并非如此。当一种解释与实证数据相一致时,这总是有益的,此为这两种理论之间的结合。不过故事模型只是对于信息处理的一种心理学解释——其并不包含对说服责任的解释。这是对相对似真性的重要补充。它揭示了诉讼框架和自然推理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当事人去阐明和捍卫对所发生之事的解释,从而导致在这些替代性解释中做出选择(或由事实认定者基于这些替代性解释构建出其他解释)。此外,“故事”只是一种关于司法证明的解释形式。不管是出于何种原因,概率之争总是集中在侵权和刑事案件上,在这些案件中,常常是提出按照时间顺序叙述的故事,但还有许多其他类型的诉讼不存在这种形式的故事,比如反托拉斯诉讼,或无过错离婚以及许多合同诉讼。在这些案件或者其他案件中,竞争性解释也可以被提出,不过却未必以“故事”的常规意义形式而出现。
总结一下到目前为止的讨论:第一部分讨论了我们的进路为何比传统进路提供了更好的解释。本部分已经针对我们进路的几种可能的反对意见做了回应。我们发现,实际上没有一种反对意见能够削弱我们进路作为司法证明更优解释的地位。然而,我们还没有考察我们的批评者提出的替代性观点。或许他们有更好的解释。我们将用接下来的三个部分来考察他们的这些自信的观点。
三、施瓦兹和索伯:对合取难题的进一步检视
施瓦兹和索伯通过将传统概率性进路从合取难题中解救出来这种方式,试图复兴关于证明的传统概率性进路。显然,他们认为“合取难题”是“最严重的(证明)悖论,对概率论构成了最大挑战”。而且,通过处理该问题,概率性进路的优点得以保留。正如我们上文所讨论的,问题是从证明标准适用于单个要件这一事实而提出的,而非作为整体的主张。施瓦兹和索伯试图以更符合概率性进路的方法,重新解释陪审团指示和基本法律原则,对此事的现状进行回应。他们认为,法律实际上需要对要件的合取(而非每一要件)进行证明。阐述他们论证失败的原因,将使我们能够厘清关于所述司法证明理论的几个关键批评点,并进一步阐明解释性进路的优越性。
让我们回到合取难题的一些根据上来。传统概率论的一个定理是,两个独立事件的结合概率是它们各自概率的乘积;另一个定理是,在给出第一个事件已发生的条件下,两个相依事件的联合概率是第一个事件的概率乘以在第一个事件已发生条件下第二个事件的概率。这些理论,显然有益于考虑法律责任的基本结构。如果在任意要件实际上是错误的情况下,错误地做出对原告有利的裁决;那么,将说服责任适用于各个要件而非整个案件,将会产生不恰当的错误分配。例如,如果两个要件各自被证明具有0.6的概率,它们相互独立,则至少一个为假的概率为0.64(因此做出有利于被告的裁决是恰当的)。此问题及相关问题早在三十年前就引起了证据学者们的关注,并推动发起了尝试解释司法证明性质的学术研究。尽管就缺陷是什么以及如何回应这些缺陷仍存在很大分歧,但人们普遍一致认为,合取难题表明司法证明的传统概率性解释存在着这些缺陷。宁愿接受合取效应,只是现实世界的一个方面, 而不是任何数学结构的函数,一些学者试图通过解释合取效应及其相关问题,来努力维持对于司法证明的更为强劲的概率性解释。
相对温和一些的施瓦兹和索伯,关注的是该争论的一小部分:试图把概率性进路从合取难题中解救出来。但是,他们的论证甚至还没起步,因而无法理解为什么了解本文正在研究的内容是至关重要的。证据文献(让人产生)好奇的地方之一是,许多为司法证明概率性进路辩护的讨论,似乎没有牢牢把握或结合概率论的数学基础。当然,那些没获得数学学位的人总能或多或少成功地使用“概率”这一术语。不过,当讨论从这些日常用法中发生改变时,就会出现问题,例如,从数学用法来看,明天会下雨的概率,以及声称司法证明的最佳解释,都是数学概率。
施瓦兹和索伯似乎假设,人们可以分配代表事件发生“概率”的数字,这种陈述是有意义的,仅此而已。情况不是这样。像所有的数学一样,概率论数学是形式的,而非实体的。数学推导出(spins out)公理、定义和逻辑运算的形式含义。它必须经过解释,才可运用到现实世界的任务中,不过如上文所述,在司法证明背景下,对概率表述的任何解释都没有多大意义。这一点已在本文中有所讨论,这也是数学上高超的概率论支持者为什么会接受将主观概率作为司法证明解释的原因。正如我们在上文再次讨论的,主观概率的困难在于,它真是主观的。实际上,先验概率和似然比都是由决策者决定的。正如这一解释的创始人所意识到的,它的魅力仅在于与主观信念保持一致,而非促进对现实的准确评估。如果施瓦兹和索伯仅关注于准确的决策过程(decision-making),而非在保持一致的主观信念方面实现个人满足感的话,那么,他们的论点实际上是行不通的。
相反,施瓦兹和索伯或许想要采取相对频率的概率性进路(relative-frequency account of probability)。他们以多伯特案(Daubert litigation)中的因果关系证明为例,指出了相对似真性理论的困境,以及为什么概率性方法(probability approaches)显然更好。毒物侵权案件中的因果关系,不能代表法律系统处理证明问题的方式。这些案件实际上往往会因为某种物质(substance)导致特定的结果,从而削弱证据的强度。此类案件的证明总是具有相对频率的性质,因为这就是在流行病学研究(epidemiological studies)领域中建立因果关系的方式。而且,他们对案件的表述也很奇怪。施瓦兹和索伯似乎认为,在这些案件中,“被告没有提供替代选择”;但是,这根本就是错的。毒物侵权案中的被告,通常会在庭审中提出因果关系的多种来源作为辩解,事实认定者本质上被要求决定哪个更似真:该情况是由药剂(agent)导致的,还是由其他原因引起的。正如上文我们所讨论的,相对似真性允许双方当事人去争论他们想要争论的事项,包括那些不连贯的概率,以此来轻松地处理这些案件。
但是,抛开毒物侵权案件这样的特例,相对频率解释对一般案件的运行意味着什么?文献中预设了一种答案,但它再次证明了相对频率进路的非似真性:原告将用尽世上一半以上的方法去解决争议发生那一天的问题,以支持被告承担责任。这是一个严苛的标准,恰恰是因为通常没人知道所有可能性大约是多少,更没有人知道如何获得关于它们的证据。所以,互补公理(complementation axiom)即,原告案件及其否定的概率相加为1。对于证据的概率性进路来说,互补公理问题与合取定理的问题一样多,甚至更多。传统概率的概率空间充斥着总和为1的概率事件。这种知识简直不属于人类境况(human condition)的一部分。
这些概念性问题,以及他们无法解决它们,就是我们一开始说施瓦兹和索伯的论点不成立的原因。即使我们先把这些抽象问题放在一边,他们的论证仍有其他严重的问题。最重要的是,他们的法律解释与法律原理和证明过程都不一致。论证他们解释与法律之间的这种不兼容性,将能更详细地强调相对似真性的解释性价值。
他们的核心主张,以及他们“解决”合取难题所依据的前提,是审判中的证明要求证明(除每一单个要件之外)各要件的合取。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人们会期待陪审团指示这样说。但是,几乎所有陪审团指示都告诉陪审团成员,要将证明标准适用于每一单个要件——这将产生合取效应——但没人告诉他们去认定合取的概率。施瓦兹和索伯对这一现实进行了回应,他们反驳道,当指示告知陪审团成员“每个”或“任何”要件必须被证明达到标准时,这仅仅是满足了证明责任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未能证明任何单个要件,意味着原告没有履行证明责任,但证明一个要件是不充分的。这也为考虑要件的合取打开了空间——除了要证明每个要件达到标准(如超过0.5)之外,原告还必须证明合取也同样要超过该标准。因此,根据这一解释,在这些案件中,承担证明责任的一方虽然已经分别证明了所有要件,但未证明这些要件的合取,那将因此而败诉。施瓦兹和索伯因此得出结论认为,任何可感知的“合取难题”,都是基于这样一个简单的逻辑错误:通过混淆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误解了陪审团指示。他们声称,随着这种误解的消除,概率性进路与法律之间的契合将得到重建。
证明责任的解释因为完全缺乏任何法律支持,是完全不似真的。在没有对每个案件和每个陪审团指示进行调查之前,我们显然不能证明这种否定——即他们的立场未在法律中得到体现。相反,我们将论证他们立场的分析性缺陷,指出绝大多数支持我们立场的证据是完全不矛盾的,然后指出,如果他们当真希望尝试这样做的话,我们将证明他们是如何错误的。
施瓦兹和索伯论证的起点是这一事实,即陪审团指示会告知陪审团逐个要件地适用这些指示。通常随后的一条指示是,如果任何要件没有为适当的说服责任所认定,则应作出对被告有利的裁决。除了通过说服责任所要求的指示去认定每一要件之外,如何去理解这些其他的指示是有困难的。施瓦兹和索伯认为并非如此。他们指出(就像在他们之前南斯所做的一样),这在逻辑上是一致性的,即如果至少一个要件未被证明,则应该做出支持被告的裁决,如果各项要件的合取满足了说服责任,则应该做出支持原告的裁决。这在逻辑上是正确的,但在实践中却无关紧要。主要问题是语义的,而非逻辑的。这尽管是一个经验性问题,但实际上每个人听到类似指示都会将其解释为,如果你认定每一要件都满足了适当的说服责任,判决就应该支持原告。告诉一个外行人,如果任何要件没有被证明到优势标准就应该支持被告,这很明显传达了一个信息,即如果其刚才告知的所有要件实际上已被优势标准所认定,那就应该支持原告。如果这是错误的,那么,为什么世界上有关辩方获胜裁决的指示会故意不准确,因为没有说:“即使你通过优势标准认定了每一个要件,如果此案在整体上没有满足说服责任,那么,你仍有可能返回去做一项支持被告的裁决吗?”
此外,这里有一个分析性要点:为了提供对那个主张的正当性支持,依赖于当前指示与一些附属主张的逻辑一致性,是一种相当奇特的推理形式。各种主张的一致性本身实际上并没有正当性力量。证明责任的陪审团指示关注要件与主张的一致性,如月亮是由绿色奶酪制作的。它也与“月亮是由俄罗斯人创造的幻觉”这一明显不一致的主张相一致。在施瓦兹和索伯所倡导的推理形式下,作出陪审团指示的形式,为所有这三种主张都提供了支持,这确实是一种令人匪夷所思的推理形式。
简而言之,这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修辞。摆脱这种修辞的方法是,着眼于他们所解释的证据,包括如果其结论如果为真的话,人们将期待看到的东西。如果法律制度想让事实认定者去确定合取,人们将认为会有如此表述的指示。我们寻找了,但并没有找到。施瓦兹和索伯建议,这也许是因为制度只是假设,常人会做整体性思考(我们赞同这一点)。那么,这是否会陷入僵局?不见得。下一步要看法院如何在真实案件中实际上适用证明标准,而不是仅仅依赖模范陪审团指示。施瓦兹和索伯依赖南斯的论点,后者认为密西西比州的陪审团指示,显示出了一种合取路径。施瓦兹和索伯还断言,美国第五巡回上诉法院要求对合取的证明。我们查阅后并没有找到指示事实认定者去认定合取的单个案件,并且,我们发现在第五巡回法院和密西西比州法院,有许多指示陪审团成员逐项要件地适用证明责任的案件,并明确指出认定每个要件(element)来满足所需的说服责任,这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充分的。例如,在布雷迪诉本德堡县案(Brady v.Fort Bend County)中,陪审团被指示原告必须用优势证据标准确立他们主张的每一个要件,“如果你认定,原告已证实了其主张的每一个要件,则必须决定被告是否以优势证据证明,R.乔治·莫利纳(R. George Molina)会出于其他原因选择不雇佣原告。”如果施瓦兹和索伯是正确的,那么这个案件(以及其他无数案件)就是对法律的虚假叙述。该(陪审团)指示应该是:“如果你认定,原告已证实了其主张的每个要件,你必须接着考虑该原告是否通过优势证据证实了其整个案件。如是说,则接着要考虑,被告是否以优势证据证明,R.乔治·莫利纳会出于其他原因选择不雇佣原告。”同样,在帕尔默诉比洛克西地区医疗中心有限公司案中,密西西比州最高法院得出结论:“当诉求是缺乏知情同意(infored consent)时,原告有责任以优势证据标准去证明证据初步充分的案件(the prima facie case)的每个要件:义务,义务的违反,近因和损害。”并没有提到合取。即使在刑事案件中,虽然由于指令裁决的限制,合取论证(conjunction argument)可能会获得一些支持,但是,证据充分性的上诉审查,还是以逐要件的方式进行。例如,密西西比州最高法院在博斯特诉州政府一案的问题在于,陪审团能否认定每项要件都达到了确信无疑,而且也没有提及合取。
尽管我们没有通过所有的巡回(法院)和州(法院)来寻找这些共性,我们也请上述批评者提出证据,而不只是进行僵化的逻辑或语义论证。这不是争论谁在这场辩论中负有证明责任。我们举出大量证据证明,说服责任的标准含义,是逐要件适用该标准,我们也论证了每个相反论点的错误。在等式的一侧有大量证据,另一端却没有。我们也预测不会有。我们所讨论的这些例子是反映整个法律领域一个更大一般模式的组成部分。例如,在民事案例中,当地区法院评价和上诉法院审查争议证据的充分性,如简易判决和作为法律事项的判决时,标准被适用于每个要件而不是合取。法院评估每个要件的证据,是否足以让理性的陪审团以优势标准去认定该要件,虽然如上所述,他们这样做是根据双方当事人提供的替代性解释。法院随后不会继续评估证据对于合取是否充分。当法院评价证据是否足以支持一项定罪时,刑事案件中也存在相同的模式。法院评价是否有足够的证据,让理性陪审团认定每个要件(element)都达到确信无疑标准,而不是每个要件加上它们之间的合取。此外,逐个案件讨论温希普案的宪法性要求,集中在哪些要件必须单个被证明到确信无疑,而不是哪些要件的合取必须被如此证明。
如果施瓦兹和索伯是正确的,不仅所有这些案件都是对法律的曲解,而且每一单个涉及特殊裁决的案件也是如此。在这些案件中,陪审团被指示去核实各种各样的要件,只有当所有要件以及辩护不成立都被核实后,才能做出支持原告的裁决。我们再次审视,并未发现一个特殊裁决的案件接着继续做如下指示的单个案件:“在你们依据优势证据标准认定了原告的每一要件之后,你们必须接着认定该案是否整体上满足了说服责任。”这意味着,说服责任规则是普通案件的一般裁决规则,不同之处只是采用了特殊裁决的形式。据我们所知,没人认为情况是这样。
一个又一个案件都具有相似的模式,但无论是在民事案件还是刑事案件中,都没有提及合取。美国法律制度要求事实认定者认定要件的合取的主张,是完全错误的。对陪审团指示最自然的理解恰恰相反,对案件进行的常规指示明显是相反的,上诉法院对证明标准的常规适用也是相反的。如果在这一点上还有任何其他分歧的话,那些认为我们错了的人,应该提供一些排除这种不相关性的证据,即对陪审团指示的语言,存在许多牵强附会的替代性解读方式。
最后,即使施瓦兹和索伯关于要求陪审团成员去认定合取是正确的,问题仍然是这将意味着什么。正如我们论证过的,这意味着对所提供的各种替代性解释进行比较,以便让原告或检控方获胜,所选择的解释必须将各个要件具体化。这就是全部内容所在。施瓦兹和索伯抱怨说,这并没有“解决”合取难题。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对的,因为世界上没有什么问题是非要解决不可的。像相对似真性所解释的法律制度,通过将合取效应分配到双方当事人的案件中来改善合取问题。我们理论的要点,不是要“解决”合取难题,也不是要完美映射庞大美国法律体系中的每一单个案例,而是要促进对那种复杂系统的理解。我们认为,相对似真性比其他任何可获得的解释都更好——它如何处理合取效应只是原因之一。
南斯:决策论、认知概率和分量
让我们转向第二个例子:南斯教授的概率证明理论。他的著作是学识渊博的典范,包含了许多有关证据领域各种问题的有趣、远见卓识和有益的分析,但我们在这里只对他的证明理论感兴趣。南斯在传统概率性进路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错综复杂的理论进路,但在几个方面偏离了传统概率性进路。他的研究进路在三个主要方面不同于传统进路(第一部分讨论过):(1)证明标准之概率阈值视个案而定;(2)以“认知”概率进行证据解释;(3)对证据的“分量”(weight)要求。
在对传统路径进行这些调整时,南斯将他的方法论描述为“既非完全描述性,亦非完全规范性”。相反,他解释说,他的理论是“解释性的”,因为该理论试图解释“应该如何理解证明标准”。该理论“不需要与现行法律运作的所有细节相匹配”——相反,其旨在“阐明法律是如何运作,以及如何在保持忠于法律中隐含的基本假设和义务的同时更好地运作。”在讨论该理论时,我们认为将描述性和规范性区分开是很重要的。正如我们将在下文解释的那样,南斯的理论未能提供比我们的解释性路径更好的实证性描述。南斯可能也认同这一点。正如我们所指出的,他并没有宣称提供了一个更好的解释性进路,而是在从事一种有些模糊的(对我们而言)“解释性努力”。尽管如此,为了免生疑问,我们将证明,他的主张在描述上是错误的。另外,我们还论证了该理论的规范性方面与他所接受的证明责任和标准背后的“基本假设和义务”的不兼容性。现在我们转向南斯理论的具体内容,主要关注其不同于传统概率性进路的三个方面。
南斯理论的第一个要素,涉及证明标准所要求的概率阈值。传统进路下的阈值被假定为概率轴上的某个固定点,大于0.5的优势标准,更高标准则数值增加。南斯将此要求称之为“区分力”(discriminatory power),他否定了每个标准都有一个固定位置的传统假设。该观点通常始于该规则关于准确性和在当事人之间分配事实认定错误风险的普遍可接受性目标。正如证据法文献数十载所讨论的那样,决策论提供了将这些基本目标形式化并加以思考的有益方式。具体而言,它提供了一种将可能错误的类型(积极错误与消极错误)与成本结合起来,以及将正确结果的类型(真阳性与真阴性)与收益结合起来的框架。如果人们知道这些概率的每一个具体数值,就可以计算出“最大化预期效用”的阈值。证据法文献中通常的理论性路径,是将这个框架作为一般类别应用于每一个标准。然而,南斯将这种决策论方法运用于其逻辑结论。每个案件都是不同的,所以,每种可能的结果都将有其自身的价值。因此,他得出结论认为,阈值的大小应该因案而异。尽管这些标准旨在反映政治道德的一般考量,南斯仍坚持认为,为了对每个案件的要求进行“量身定制”(tailor),法律事实认定者可能需要对阈值进行“边际”(marginal)和“零售”(retail)式调整。
作为证明标准的一种描述性理论,这种解释与该标准运作方式的几个重要组成部分难以适应。首先,正如南斯所承认的那样,这并不是实际的事实认定者裁决案件或者从证据得出推论的方式。在这一点上,我们似乎与他的“解释性”路径存在根本的方法论分歧。我们认为,符合这些推论的实践情况,对于解释证明标准是至关重要的(不过,也许他的“解释性”方法论将他的分析从这些束缚中解放出来了,在此情况下,他和我们仅仅只是追求不同的目标)。确实,南斯承认在事实认定过程中,解释和解释性推论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他提出,概率性阈值基于其他标准因案而异,而不是将这些角色与证明标准联系起来。第二,在“零售”层面设置概率性阈值的标准,一般不会反映在陪审团指示中:例如,事实认定者不会被告知,通过考虑与不同可能结果相关的效用去“调整”这些标准。有人会认为,如果这是法律试图要实现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那么,陪审团成员将被告知去这样做以及如何这样做。第三,双方当事人一般不会,而且通常也不被允许提供与这些结果相关效用的证据。第四,讨论这些标准的司法意见,并没有做出这样的零售调整,或者考虑由理性的陪审团在评价证据的充分性时作出可能的调整。法院考虑一个理性的陪审团能否得出证据满足了固定标准的结论,但他们并没有考虑,理性陪审团在概率尺度上能否确定该标准的阈值。第五,在认为正当程序要求将“清晰且令人信服的证据”标准适用于终止父母权利的程序时,美国最高法院已明确警告该理论所提出的可变性类型:
本法院从未批准过在特定程序中逐案确定适当的证明标准。证明标准如同其他“程序性正当程序规则一样,在发现真相的过程中由固有的错误风险所塑造,其适用于案件的一般情况,而非罕见例外。”因为诉讼当事人和事实认定者在给定程序开始时就必须知道将如何分配错误风险,证明标准必须预先被刻度化。
总的来说,这些特征表明,南斯的理论是对当前证明标准的一种糟糕的描述性进路。我们赞同,决策论考量对准确性与错误风险的法律制度目标提供了一种有用的形式化方法。在实践中,法律试图实现这些结果的最佳描述性进路,是通过考虑不同可能的解释(根据不同的解释性阈值),而不是通过要求陪审团成员和法官(无论明示还是暗示)去做出关于最优概率性阈值应该是什么的与众不同的判断。
然而,该理论也具有规范性的雄心,尽管这些雄心的范围是模糊的。南斯一方面认识到,一个不受约束的、个案预期效用方式存在着理论与实践的障碍,然而另一方面,他似乎支持事实认定者的个案调整。他的怀疑主义赢得了胜利。的确,如果目标是最大化预期效用——以及每个已知可能结果的个案效用——那么,该理论的缜密性将是对传统概率性进路的改进。毕竟,作为一个正式事项,在每个案件中的最佳结果,都比在某些案件中不能最大化效用的分类阈值更可取。但是,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中,将可变的证明标准强加给传统进路,会将大量的复杂性和信息成本引入证明过程。每一个可能的案件都必须设想先验概率并提供一种规则,或者当事人(或法院,鉴于南斯以法院为中心(court-centric)的证据法观点)将必须为具体案件建立适当的效用函数(utility function)。当然,这反过来又取决于事实究竟是什么,我们认为,在大多数诉讼案件中,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因此,可以推测,相关事实的概率将会被认定,接着另一轮诉讼将会发生在当事人对与相关事实的真实性概率有关的效用提出质疑之时。坦白地讲,我们简直不知道这样的争议会变成什么样子。
或者,人们可能采取主观路径,仅仅指示事实认定者考虑相关效用(utilities),正如南斯所建议的那样。他们必须这样做的依据是什么?随机的外行人,或者在此方面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士,怎么知道如何根据其他人(立法机关,法院…)的预期效用偏好,来对个案进行调整呢?当事人可以提出什么样的证据,来理性地解决此类问题?人们可以接受主观性,并告诉事实认定者去按照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做出调整,但很明显,这将会导致基于无知信念的特殊标准的引入。除了事实认定者个人的自我满足之外,这将如何提高任何人的预期效用(utility)则完全是一个迷。
除了与计算标准相关的问题之外,该理论还继承了困扰传统路径的所有其他问题。首先,南斯的理论与传统进路一样,为了实现其决策——理论的结果,标准必须适用于整个案件而不是各项要件。因此,合取难题再次出现了。当阈值被应用于各项要件时,该理论在准确性和错误风险方面产生了次优结果。这就是为什么南斯试图将此类要件加上它们的合取要求写入法律中的原因。第二,基于其理论的证明标准也如传统进路一样是非比较性的,一旦每个标准的阈值固定之后,他们会假定每个要件与它的否定命题相加为1。因此,出于类似原因,它不太可能会促进法律的基本目标。传统进路的最后一个问题涉及对证据量化的需要,数字需要与固定阈值进行比较。不过,正如我们上文所讨论的,这种基于客观数据或主观信念进行的量化,遇到了困难。南斯的理论也需要数字,并且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它也会遇到与传统进路类似的问题。这个问题将我们带入了该理论不同于传统进路的第二个方面。
该理论的第二要素依赖于“认知”概率的特定进路。南斯认识到,问题依赖客观(频度)或主观(确信)概率,继而提出审判中的目标概率是“认知的”(或“理性的”)。在此种解释下,概率是指基于证据(形成的)“理性”或“被证成”的信念程度。他解释说,这些概率为事实认定者的实际主观信念提供一个规范性标准:“一个人认为某个命题为真的主观确信概率,应该等同于这个命题的认知概率,该命题是根据(相对于)已拥有的证据来确定的。”此外,认知概率“必须符合数学概率的公理。”在这种观念下,“所有理性人”,在“给定相同证据”的情况下将具有相同认知概率。
不过,对“认知概率”的依赖,减少了他试图避免的相同困境。的确,在裁判背景下,该理论的概率概念似乎与主观概念没什么不同。我们对此解释一下。让我们假设存在这样的认知概率,即在给定证据的情况下,对于某一特定命题,每一个理性事实认定者都必须具有一定的信念程度或证成的层级。这种概率将是既可知又不可知的。让我们假设它是可知的。我们怀疑大多数证据或证据集合体都将是这样,但如果它存在,那么根据定义,这就是唯一可以达成的理性裁决。这些案件将永远不可能进入审判。另外,在此类“认知概率”已知的案件中,将包含逻辑真实(很少进入诉讼),否则它们几乎肯定会符合已知的“客观”频率概率。简而言之,知道正确的“认知”概率将是诉讼中罕见的例外,特别是在进入审判的案件中。
在大数案件中,所有理性代理人(rational agents)必须达到的认知概率将是未知的。不过,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该理论减少了概率的主观性观念。在一段生动的文字中,南斯断言,即使裁判的目标是认知概率,“事实认定者仍将不可避免地使用自己的主观概率。”不过,在解释其理论如何映射到由事实认定者做出的实际评估时,他再次依赖于主观评估:
出于实践目的,例如裁判,重要的是,能够对认知概率不可避免的主观评估做出比较性断定,包括粗略的定量比较,例如对于数字r,断言p(C|E)或多或少(粗略地)等于r乘以p(not-C|E)。
此处的关键点在于:(1)告知陪审团成员基于证据作出主观评估;与(2)告知他们基于证据作出他们认为认知概率是什么的主观评估,其实两者没有区别。任何注意到这两者之间存在区别的事实认定者,都会改变他们的主观评估以符合他们所理解的认知概率,至少在他们试图变得“理性”时会是这样。但是,出于所有相关的目的,当陪审团成员做出他们的主观概率决定仍然是一个主观概率概念时,告诉他们要“理性”并要“审查证据”。
因此,南斯面临着和传统路径一样的困境,他的理论需要为证据赋值。我们如何量化证据,而与证明标准进行比较?对于这个数值应该是多少,要么有一个正确的“客观”答案,要么没有,应该有一个正确“客观的”答案。如果该数值是已知的,那么事实认定者几乎没什么可做了。这是唯一合理的答案。但是,这种情况在诉讼案件中很少见。这些数值在标准案件中并不存在,或者是未知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别无选择,只能依靠基于证据的主观评估。不管采取何种形式,如,“我认为琼斯犯下谋杀罪的可能性是0.95”,或者“我认为关于琼斯犯下谋杀罪有多大可能性的正确答案是0.95”,都存在同样的问题。
最后,南斯的理论与传统概率性进路的第三个不同之处在于,他为证明标准建立了一种“分量”要求。根据该理论的这一要素,当事人除提供证据外,还需要做更多的事情,以便理性的事实认定者能够得出结论认为,所适用的证明标准(在其理论下,是指“可变阈值”)已经被满足。除了提供充足的证据来满足该标准之外,“请求方必须提供其理应提供的任何证据,以确保证据足够完整。”不承担证明责任的当事人,负有对等的义务。例如,在民事被告的案件中,这些包括:(1)有证据表明理性的陪审团能够得出结论,认为该标准尚未得到满足;以及(2)“被告必须提供其理应提供的任何证据,以确保证据足够完整。”未能满足任意一项要求的话,根据该理论,将会导致一项作为法律事项的裁决来反对被告。在陪审团审判中,该理论将劳动分工适用于这两项要求:陪审团决定证据是否超过标准阈值,法官决定所提出的证据在分量上是否足够。如果法官判定证据性基础不充分,那么,作为一个法律事项,该标准就没有被满足,即使证据足以使理性的事实认定者得出结论,认为已经满足了该标准。
尽管南斯曾一度承认,“分量监控功能”对于证据充分性的决定并未“明确构筑入传统标准之中”,他声称,要揭示这种决定中隐含的分量原则。此外,充分性规则只是法院用来规制分量的一种学理方法(doctrinal device),其他还包括可采性规则和证据开示制裁。即使法院没有明确或“自觉”引用分量原则,此类方法的使用是“作为优化(或至少稍微改善)凯恩斯主义分量(Keynesian weight)的最佳解释”。他的理论汇集了法律实践的证据,尝试去解释隐含在法律中(连观察者和参与者自己都没有注意到的)的原则:
这里回顾的一系列法律工具的存在和使用表明,在允许证据开示及其实施过程中超出常规影响(regulative affect)的情况下,对于某些裁判官员是否需要担心凯恩斯分量的扩张,给出了答案,尽管答案并非总是清晰和明确的。
如同南斯的解释理论不同于传统概率性进路的其他方式一样,该理论的分量要求未能解释法律。让我们检视一下有关该原则的一些证据。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在所引用的支持分量要求的案件中,既不能为该要求提供任何支持,也难以通过其他的考量因素来做出更好的解释。不过,有必要澄清一下。我们将南斯关于司法证明性质的解释性主张视为是对现行法律的解释。因此,我们把他援引的一些旧案件放在一旁,这些案件是现代证据开示制度出现之前作出的。在现代证据开示制度中,法院扮演了更为积极的角色,试图迫使当事人提供证据。当我们转向更现代的案件时,关于司法管控分量要求的证据是很弱的。
南斯指出证据来源之一,是涉及“证据充分性”判定的案件,这些案件据称是支持该理论的依据。根据该理论,当证据满足两项要求时就是充分的:理性的事实认定者能够得出结论说,证据超出了证明标准所要求的阈值;以及,法官可以得出结论说,证据完整或有足够的分量。南斯援引了波斯纳法官在第七巡回法院的意见,认为原告在庭审中的证据根据优势标准足以支持一项裁决。该案与滑倒受伤有关,原告声称,被告的一名叫不出名字的员工应该对其受伤负责(把肥皂水洒在了原告摔倒的地方)。尽管审判法院和上诉法院均未要求超出当事人自己选择出示的证据以外的任何证据,南斯还是注意到这种司法行动的可能性,他的观点如下(我们重复了他的原话):
不仅没有理由怀疑原告隐瞒了不利的证据,而且鉴于种种风险,指望其进行更彻底的调查也是不合理的。这是一个小案,但并未小到可以不经意地将其从联邦法院系统排除,只是小到它会使试图强迫当事人去提供更多证据变得毫无意义。正如我们所说,我们没法从证据缺失(the paucity of evidence)中得出结论说,原告害怕做出更细的调查,因为担心她会发现是顾客而不是沃尔玛员工洒下了肥皂水。
南斯的主张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当案件涉及“更大赌注”时,波斯纳法官将会愿意考虑要求原告提出更多的证据。分量原则当然也符合这一观点。但是,有三件事与这种解释相悖。第一,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论点。它断言,一个案件实际上与它所持的观点相反,该观点是按照关于法院在未审理之前可能做什么的意见,从模糊性判决所作的推测。南斯不是从反事实的角度来为自己辩护,而是应该提出一些实际的例子来证明其断言为真。第二,解读波斯纳法官评论的更自然的方式是,在很大程度上,法院可能倾向于有所作为,如果其认为原告是以某种不利于被告的方式在玩游戏的话。这不是分量问题,而是证据开示问题。我们预测,如果法院认为存在更多的证据,而且双方当事人都能获得这些证据,那么,这些案件的结果将是相同的。做出这种预测的原因,则是南斯论点要面对的第三个困难,即该法院以及全国各地法院的大量案例解释表明,在提出证据和辩论争点时,当事人是“他们自己案件的主人”。一般而言,法院援引“案件的主人”原则后,绝大多数都倾向于遵从当事人的证据选择和出示。后一原则比法官管控和预测当事人证据选择的分量要求,更符合法律。
但是,即使由当事人做出的选择明确主导了司法分量管控,正如我们主张的那样,大概在一些明显的案件中,分量确实是最佳解释?暂且抛开暗示这种监测之可能性的观点,对于南斯进路的最佳证据将是有关充分性的案件,在这些案件中满足了第一个要求但却未满足分量要求。换句话说,在原告的案件足以使理性的陪审团根据优势证据作出支持原告的认定的情况下,但法院仍然认为证据不足。南斯以齐赫(Zych)案为例做了详细讨论,他声称,该案提供了一个对“有关凯恩斯分量的司法要求”之“惊鸿一瞥”(revealing glimpse)。然而仔细研究该案后,就会发现它并不支持这种说法。
齐赫案是一个海事案件,在该案中,原告寻求确立一项发现于密歇根湖底的一艘废船之物权。原告声称,该船是1868年沉没的一艘客船,名叫海鸟号。为什么此案被认为可以支持分量要求呢?根据南斯的说法,“决定性的事实是该沉船是否 ‘埋置于’该州淹没的土地中,如果是的话,该州(伊利诺伊州)就对该沉船拥有更好的所有权凭证。地区法院因为该船“很可能被埋置”,批准了该州的驳回动议。正如南斯所解释的那样:法院是基于诉状和动议文件,并且在“未听审正式证据”的情况下这样做的。然而,“上诉法院撤销并发回重审了该案,要求就沉船是否埋置进行证据听证”。换句话说,它看起来像是一个符合前述理论两部分结构的案件。看起来地区法院似乎做出了一项(“很可能被埋置”)的事实性认定(即原告通过优势证据证实了这一事实),并且上诉法院撤销原判——不是因为它不同意这一认定的合理性——而是因为它得出结论认为,需要进行证据听证。根据南斯的说法,上诉法院关注的是证据分量。
齐赫案的细节显示了它并不支持分量要求。一个线索是存在争议的意见涉及驳回动议。双方当事人都没有请求一项关于埋置的事实认定。从地区法院的命令中可以清楚表明,法官将“埋置”问题定性为法律问题。法院援引了其他案件的一般主张,即“被遗弃的沉船通常被认为‘埋置于’淹没的土地。”显然,法院的理由是,只要船只沉没了,那么不管该船的任何部分是否被掩埋和贴地,都“很可能被埋置”:
考虑以上援引的案例,依据《淹没土地法案》(submerged lands act),沉船很有可能埋置于该州拥有的淹没土地中,而普通法中认定的埋置例外,赋予了该州一个在沉船事故中貌似有理的(colorable)所有权主张。
在撤销原判的过程中,上诉法院所做的不仅是命令一项证据听证。首先,它指出,地方法院的命令是基于错误的法规。第二,它解释道,根据所适用的法规(《废弃沉船法案》),“埋置”是一个有特殊含义的“事实问题”。出于该法规的目的,“埋置”要求做出一项关于该船只残骸“至少部分被掩埋”或“牢固地贴地”的事实认定。因此,法院撤销原判并发回重审,其解释说,需要进行证据听证以确定该事实问题。但是,在发回重审中,并没有举行证据听证。相反,正如该地区(法院)所解释的那样:
在发回到本法院后,当事人在没有举行上诉法院所建议的证据听证的情况下,解决了“埋置”问题。为了回应该州提出的承认请求,齐赫在本诉讼中承认了海鸟号[被埋置]……当事人和法院都承认这个证据的采纳是充分的。
正如这些细节所表明的,此案与在司法上强加的分量要求无关。审判法院在第一次审判时,没有做出事实性认定(双方当事人也没有要求)。而在第二次审判时,法院尊重了当事人不对争议事项提供证据的选择。与其说这是一个关于法院推翻了当事人对于证据选择的案件,还不如说是一个没有证据被提出的案件,因为当事人没有选择将其作为一项争议来处理。
南斯试图将分量要求解读为可采性裁定也同样存在问题。例如,他引用钱伯斯诉密西西比州案来支持一项分量要求。该案涉及被告被制止提供第三方有罪供认的证据(通过整合该州阻止当事人弹劾己方证人的传闻规则和“担保”规则(“voucher” rule))。出于几方面的原因,我们发现这是一个奇怪的案件。重要的是,被告传唤第三方作为证人(是为了弹劾他),并且被告还试图提供被排除的证据。更一般地说,钱伯斯案被一系列界定为被告拥有进行辩护的宪法性权利的案件所遵循。此案并不是关于法官通过宣布一方的证据不完整就推翻当事人选择的案件。南斯声称,该意见“具有增加凯恩斯分量的效果。”那又如何呢?增加分量并不能解释该裁定。正如该法院所论述的那样,在考虑有关提出辩护权利的其他案例时,这些案件被解释为:(1)排除证据规则的任意性,以及(2)被排除证据的可靠性。这两种考虑因素都不一定与分量有关。例如,当法院裁定被告不拥有引入测谎仪证据的宪法权利时,这是因为证据的可靠性存在问题,以及政府排除可靠性存疑证据的权益。不过,倘若允许被告提供该证据,将会“增加凯恩斯分量”。
这些观点相当尖锐地挑战了南斯关于分量原则存在的描述性主张。证据完全是相反的。另外,上面的例子也对这一原则的规范性提出了质疑。南斯论述几种使分量要求更为有力的方法,主要有成本、实用性和证据的重要性等问题,以及当事人采取了合理、疏忽还是不诚信的行为,以致未能提供法官认为应该有的证据。由于以下两个原因,我们先把有关这些问题的理论之其他细节放在一旁。首先,我们怀疑除了证据开示需求和制裁之外,更有力的司法干预是否可能提高结果的准确性。当事人(至少在民事案件中)往往比法官更加了解自己的案情,并且在确定提出哪些争点以及如何最好地证明这些争点方面,有着明显的自身利益。总之,我们可以在“案件的主人”这一原则中看到相当大的智慧。即使齐赫案中的法院认为证据听证会是最好的,当事人却不一定这么认为。其次,即使有必要对证据决定进行更多的司法事后审查(second-guessing),我们仍然怀疑“分量”而非可靠性,应该是控制原则。正如谢弗案表明的那样,不可靠的证据可能会增加分量。如果要在“更有分量但更不可靠”与“分量不够但更可靠”的两个证据性基础之间进行选择,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人选择前者。
总而言之,南斯提出了一种详细而复杂的理论,该理论与传统概率性进路有着三点重要的不同:因案而异的证明标准阈值、认知概率和分量。尽管做了许多修正,他的理论与传统进路一样,未能提供一个比相对似真性更好的解释。
克莱蒙特:魔幻现实主义、模糊集合(fuzzy set)与信念函数
我们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例子,是凯文·克莱蒙特(Kevin Clermont)最近试图用“模糊集合理论”和“信念函数”来解释证明标准。他声称,从这些概念视角来审视法律,可以解决合取难题,并构建一个比所提出的任何其他理论(包括我们的理论)都更好的司法证明解释。像我们讨论施瓦兹和索伯以及南斯的观点一样,我们将论证,克莱蒙特的司法证明进路也未能提供一个比相对似真性更好的解释。
上面标题中使用的“魔幻现实主义”,是我们而不是他命名的。尽管该术语在艺术批判主义中有悠久的历史,但随着1982年加布里埃尔·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 Garcı´aMa´rquez)成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魔幻现实主义”才在文学界崭露头角。该术语包含许多不同的理念,但其核心信条是将现实主义与神秘主义元素相结合,可以提高读者对他们自身现实感的鉴赏。克莱蒙特教授的理论让人联想到魔幻现实主义,因为他将冷静分析与不切实际的魔法因素结合在一起。他的分析在对复杂法律的清晰阐明方面具有启发性,并体现出其惊人的学识。问题在于,他理论的核心方面,如同加西亚·马尔克斯对时间描述一样,实际都是虚幻的,因此难以对法律进行解释。他确实走的如此之远,以至于他论证的一部分“可能听起来像魔法”。正如我们将表明的,它的确如此。
克莱蒙特的理论依赖于两个核心观念的结合:模糊集合与信念函数。这种结合产生了一种与传统概率路径不同的司法证明理论,体现在两个基本方面。首先,依赖模糊集合理论,克莱蒙特否定了两个或多个命题结合的合取定理。第二,依赖信念函数,他否定了一个命题的概率及其否定命题之和为1的互补公理。克莱蒙特认为,这种结合提供了一种比传统概率性进路或相对似真性进路更好的证明标准描述进路。在讨论了他理论的每一个组成部分后,我们认为并非如此。
克莱蒙特理论的第一个核心理念是“模糊集合”。模糊集合论致力于用“集合隶属度”(membership in a set)概念来解决语言的模糊性问题。想象一下高个子集合。高的含义是什么?它是模糊的。但根据模糊集合论,一个人越高,他或她隶属该集合的可能性越大,以至于或许一个身高5英尺11英寸的人隶属该集合的概率只有0.7,而一个身高6英尺10英寸的人隶属该集合的概率有0.95:“模糊逻辑主要涉及,在我们自然语言中出现的关于含混或模糊术语的量化与推理。在模糊逻辑中,这些模糊术语被称之为语言变量……模糊集合论的潜在力量在于,它使用语言变量而不是量化变量去表达不精确的概念。”模糊集合论的一个特征是,它将两个模糊集合的交集定义为,这两个集合中较低者的隶属程度。克莱蒙特试图利用集合论的这一特征去解释证明标准,但是,因为其是建立在模糊集合论的误用和数学逻辑的错误基础上,他的解释难免失败(我们将在下文详述)。
由于接受证明标准适用于单一要件,他争辩说,模糊集合论解决了合取难题。他声称,该问题“在模糊逻辑的力量之下瓦解了”,因为“MIN运算符提供了合取信念将与可能性最小的要件相匹配。”换句话说,“根据MIN规则,适用于逐项要件的证明标准,与适用于整个合取故事的证明标准之效果等同。”举个简单的例子,对合取难题的传统描述是,两个独立事件的概率,为它们各自概率的乘积。如果问题是,诚实地对一枚无偏倚的硬币做两次抛掷,得到两个人头朝上的概率是:0.5 x 0.5=0.25。正如我们已经详细论述过的,这种应用对于具有多项要件(甚至对条件依赖进行控制)的案件而言,是显而易见的,同时也是潜在令人不安的。克莱蒙特教授暗示说,并非如此。因为,所有要做的就是,将这个问题设想为模糊逻辑的问题,然后,魔法般地,合取“概率”变成了0.5!
克莱蒙特将模糊集合论应用于司法证明,存在着四个主要问题:第一个,改变人们的概率论,并不会改变这个世界或人们关于这个世界的知识。这是一个基本观点,但是,它揭示了克莱蒙特的理论与法律中事实的不确定性之间的尴尬契合。第二和第三个问题是更为技术性的(尽管我们将尝试让普通的法律读者也理解这些讨论),并且涉及模糊集合论的错误运用。其中,包括将集合的交集与要件之间的合取混为一谈,以及混淆了模糊集合与隶属关系语句(membership statements)。每一个都涉及数学逻辑的基本错误。第四个问题涉及对司法证明过程的错误建模,这在某种程度上使得模糊集合论看起来比实际更合理。我们依次讨论这四个问题。
首先,目前尚不清楚,主要解决语言模糊性的模糊集合,其隶属度如何映射到审判中事实的不确定性问题。克莱蒙特给出了以下图像,来支持模糊逻辑相对于传统概率的优越性,并“指出了法律处理的重点”:
假设你在沙漠里长达一个星期没有喝水了,然后,你拿出两个标注K和M的瓶子(分别标注:可饮用水模糊集合的隶属度为0.91,可饮用水的概率为0.91),(你)面对这对儿瓶子,并考虑必须选其一饮用,你会选择饮用哪一瓶?大多数人在接受该实验时,可能会立即看到K包含沼泽水,但其可能不会……含有诸如盐酸等液体。也就是说,0.91的隶属度意味着,K的成分与完全可饮用水非常相似……。另一方面,M可饮用的概率“等于0.91”,意味着经过长期实验,大约在91%的实验中,M的成分被预期是可饮用的;剩下9%的成分将是致命的——大约十分之一的几率。因此,大多数被试者会选择喝沼泽水。
他没有解释,该例子是如何映射到司法证明上的。为了以一种有效的方式映射到事实不确定性上,案件中两种形式的信息都必须可以系统地获得作为证据,即要么形式可以互换而解决当前的问题,要么人们通过改变自己的概率观念可以改变世界。关于司法证明有两件事是显而易见的。其一,包括克莱蒙特教授在内,想必我们都同意,水瓶中的成分,将不会因为采用的是模糊观念还是概率观念而改变。另外,事实认定者,就像我们的沙漠流浪者一样,要么知道(或相信)每一瓶都有91%的机会是水,要么相信它是91%的纯净水,要么他们都不知道。改变概率观念,不会魔法般地把瓶子中的东西,或者人们关于这些东西的知识,从一个转变为另一个。世界就是这样,它不会因为一个人概率观念的改变而改变。
这不仅对单个事实问题而言为真,而且对合取难题也是如此。模糊逻辑不能消除或“瓦解”合取效应,因为其是这个世界的一种特征——不是通过改变一个人的概率理论,就可以魔法般地改变的东西。事实认定者随时都需要决定两个或以上争议事实问题,它们中的每一个,对于做出支持当事人的认定而言都是必要的,任何错误的决定都会造成错误(并且错误将会随之累积)。它们全部为真的概率,不是“可能性最小要件”的概率,就像连续获得两个人头朝上的概率不是0.5(而是0.25)。合取效应是这个世界的特征(而且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它不会因为发誓效忠模糊逻辑而发生改变,就像瓶子中的东西不会改变一样。
克莱蒙特教授说,事实并非如此,他断言,“模糊逻辑告诉我们,即使是独立事件,也适用MIN运算符”,甚至是对不确定性问题而非模糊性问题。在评论一个同时具备不确定性(身份)问题和模糊性(过错)问题的假设时,他说,“尽管(在这种情况下)MIN规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选择,但我认为,如果两种事实认定的百分比仅测量了随机的不确定性,它也应该适用。考虑另一个强调为什么这是错误的例子。盗窃的经典定义是,以永久剥夺财产所有权为目的,偷走他人的私有财产。假设双方当事人就是否为偷走存在争议(也许物品丢失了或涉嫌欺诈),如果是偷走的,那么是谁干的(可能误认),以及是否有永久剥夺的意图(可能是个恶作剧)。进一步假设(虽不切实际,却有助于做出必要的分析),在所有证据都被考虑之后,事实认定者得出结论:(1)有0.9(或者任何满足确信无疑的证明)的几率是偷走的,(2)有0.9的几率是被告人干的,(3)有0.9的几率他是以永久剥夺的意图这样干的,以及(4)这些事实都是随机独立的。很明显,事实认定者在任何或所有这些问题上,都可能是错的,而传统概率明确告诉你,这些情况都很可能发生。三个事件均为真的概率是:0.9 x 0.9 x 0.9=0.729,这意味着,发生其他事件的概率为1.0-0.729=0.271,这可能无法证明确信无疑。所有这些均完全独立于语言的模糊性,即在案件中,没人争论什么是偷走、身份和意图的含义。然而,即使在他们争议模糊性的其他案件中,不确定性仍然存在。要想让克莱蒙特教授在与合取有关的文献中添加任何内容,他一定会说,如果我们仅从模糊集合、隶属关系语句或其他方面来考虑这些问题,那么,合取难题就消失了。但这仅是在不确定性消失的情况下才会发生。然而,不确定性不会消失。他说,他并没有声称我们思考事物的方式可以改变真实世界,但在他看来,他认为自己的方法解决了合取难题,这是他必须坚持的。
我们现在转向第二和第三个问题,它们涉及由数学逻辑的基本错误而导致的模糊集合论的错误应用。第二个问题是,数学上的概率合取与集合理论中的集合交集,这两种不同概念之间的合并(或许部分原因是集合交集有时被混淆成集合“合取”)。这两种概念是不一样的,没有任何形式可以让其中一个转变为另一个。虽然克莱蒙特用MIN运算符定义集合的交集是对的,但这并不能保证得出两个或多个事件的概率合取等同于可能性最小的事件这一结论。这两个概念是完全不同的。当事件被认为是模糊集合时,也不能保证得出这样的结论。
集合论定义交集的理由是,它测量的是集合具有的相同隶属度,而不是测量一个事件或另一个事件在确定的概率空间内将会发生的概率。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一点,请考虑以下图表:(1)在1-10之间的所有质数集合;(2)1-20之间的质数集合;以及(3)在1-100之间的质数集合。它们的交集,也就是克莱蒙特教授所说的合取,是整数2、3、5和7。现在问一个不同的问题。假设从整数1-100的集合中随机抽取,那么,随机抽取的数字在三个原始集合之一的概率是多少?很明显,其随着集合的不同而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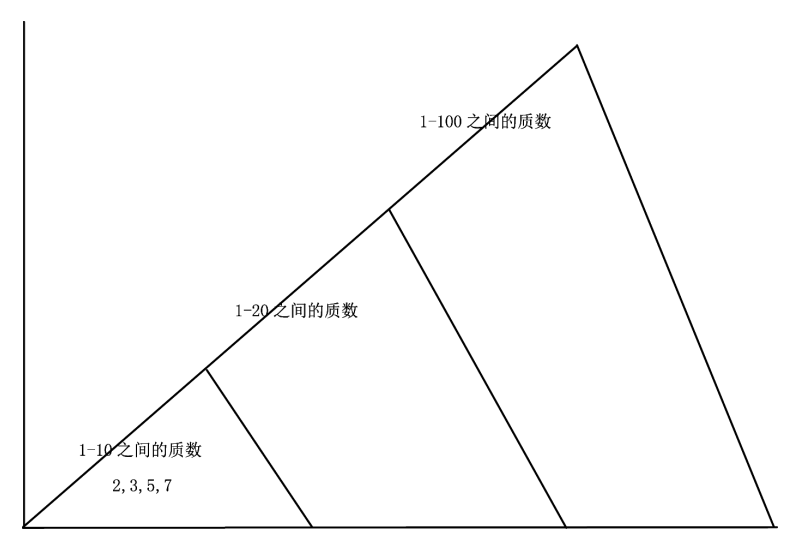 明白这一要点,至关重要。不确定性的知识,与在模糊集合或明确集合中观察到的隶属度知识完全不同。它们不能通过指令就发生相互转化,这一指令即克莱蒙特教授的理论所宣称的,通过将要件的合取等同于集合的交集。
明白这一要点,至关重要。不确定性的知识,与在模糊集合或明确集合中观察到的隶属度知识完全不同。它们不能通过指令就发生相互转化,这一指令即克莱蒙特教授的理论所宣称的,通过将要件的合取等同于集合的交集。
本质上,克莱蒙特的论点忽视了在模糊集合论中集合交集的含义。模糊集合交集并不处理两个要件均为真的可能性,或两个不同元素隶属同一个集合的可能性,或一个元素隶属多个集合的可能性,或任何其他的概率观念。而是,“在模糊集合中,一个元素可能部分属于具有不同隶属关系的两个集合。一个模糊交集是在同时包含每个元素的两个集合中较低隶属关系的集合。”换句话说,实际上,克莱蒙特将对某个单一元素在两个或多个模糊集合中的隶属度的测量,视为两个或多个要件为真的概率替代品。
由于一个数学逻辑的错误,第三个问题与其涉及模糊集合理论的类似误用有关。一方面,克莱蒙特的理论混淆了隶属关系语句,另一方面也混淆了模糊集合。他举出以下例子来表明他所声称的模糊集合交集的含义,但该例子所表明的并非如此:
从两个隶属关系语句开始……汤姆有0.30隶属于A[A=高],以及0.4隶属于B[B=聪明]。这些数字表示:“汤姆不那么高”和“汤姆不那么聪明”。
这种模糊的结合将会得出:“因为汤姆没那么高也没那么聪明,所以,汤姆不是一个又高又聪明的人。”……在这一交集中得出了0.30的信念。
如上所述,模糊集合的交集确实是如他所描述的那样被定义的,但是,模糊集合的定义并未扩展到隶属关系语句,隶属关系语句并不是集合(当然,它们可以是集合的隶属)。正如在明确集合论和逻辑学中一样,集合交集的定义是一回事,对于逻辑运算符“逻辑与”和“逻辑或”的定义则是另一回事,概率含义更是另外一回事。这个例子最特殊之处在于,你可以确切地知道,汤姆到底有多高且有多聪明,而不必去评估汤姆不那么高且不那么聪明的可能性(这一交集的信念是0.30)。这就是首先在高和聪明上产生的隶属语句。无论隶属函数是什么,在高的模糊集合中一定身高的隶属度是0.3,在聪明的模糊集合中一定智力的隶属度是0.40。集合中的模糊性,并非隶属语句中的模糊性。的确,模糊集合论的支持者认为,这类问题属于概率问题,这与人们能够将集合交集的定义以及将其运用到隶属关系语句中(如同克莱蒙特在他的例子中所做的那样)的观点大相径庭。从模糊性的角度来讨论各种概率问题是完全一致的,例如,隶属模糊集合事项的概率,不确定性与模糊性的相交等等。现在许多人从事这个领域的研究并发展了模糊概率论。但这并非克莱蒙特所假设的。概率理念并没有发挥作用,起作用的是模糊性理念。你知道汤姆隶属于既高且聪明的模糊集合,并确切地知道其为真的程度。
克莱蒙特教授可能反对这一观点,因为对一个人身高或智力的观察可能是不确定的,而且可以用模糊语言来表达。两者都正确,但无论不确定性和模糊性将是什么,都不会改变以上的分析。这的确突显了克莱蒙特分析的另一个问题。模糊集合的使用,要求隶属关系函数允许从观察到模糊集合的算法映射。克莱蒙特从未给出一个实际隶属关系函数,因而忽视了这一点。我们在上面给出了适用隶属关系函数的最明确解释,但应当承认,其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不过,分析性要点仍然存在。
模糊集合应用的第四个问题,涉及审判中证明问题的错误建模。这种错误建模使得克莱蒙特关于合取难题的分析在实际中似乎更具有似真性。他给出一个涉及模糊概率与传统概率相结合的案例,并多次重复类似的案例,仿佛这种结构是范式。假设有证据表明,汤姆有60%几率实施了某种行为(一种传统概率测量),以及,无论行为者是谁,他都有70%“几率”(一种模糊测量)“存在过错”,这里克莱蒙特教授指的是需要承担责任。根据克莱蒙特教授的(说法),当一个人整合了60%几率的“身份”和70%隶属于“过错”的集合时,运用模糊合取概念,有责任的概率应该被认定为60%。
想了解错误建模,我们需要理解“过错”的含义。克莱蒙特教授的脑海里有一些无疑会是“过错”的范例。例如,一个驾驶员看到交通灯是红色的并有足够时间停下来——此外,还看到行人正进入十字路口——尽管如此,他还是在不顾行人安全的情况下决定继续通过该十字路口,完全无视禁止闯红灯的法律义务。现在倘若把这些假设中的一部分拿开,如此一来,这个人的行为就没有那么极端了。例如,这名驾驶员越靠近十字路口,他的“过错”就越少,用模糊集合术语很容易理解这一点。这的确是克莱蒙特教授所说的隶属模糊集合的一个很好的例子。但这里存在一个问题。当作出将某一风险集合等同于疏忽的决定时(也许还会上诉),接着事情就结束了。有一个可以想象的更极端的事实集合(从做错事的角度来看,比实际发生的“更极端”),它与这些行为之集合与构成“过错”还是“疏忽”都不相关。一旦做出决定,将一组事实假设为集合,如果为真,便等同于过错,则特定要件便被证实具有确定性。所以,由于法律术语的含义,这里的“合取”将一个要件设置成0.6,将另一个设置成1.0——如他所说,但并非由于他的原因,确实等于0.6的合取概率。
最后,我们现在转向克莱蒙特援引支持其理论的另一个核心理念:信念函数。信念函数是邓普斯特·谢弗(Dempster-Shafer)理论的一部分,它是在不确定性情况下将推理形式化的另一努力。克莱蒙特并没有详细地阐述这一基本理论,他既没有对该理论进行批评也没有提出该理论在某些情况下已经被指出的成问题的后果。相反,他的理论只是利用其一个方面:即信念函数允许某一事实及其否定命题的概率之和小于1的信念,换句话说,证据也许对争议事项遗留下一些剩余的怀疑。
由于上文已详细讨论过的理由,我们在这里完全同意克莱蒙特教授的这一观点,即信念不需要加合为1。所谓绝对概率或以所有可能证据为条件的概率,都不是审判中的证明标准。审判中的证据几乎从来没有——可能永远也不会——完整地描绘出已成为争议问题的那一天可能发生之事的所有可选方案的全部图景。因此,像我们所争论的那样,以比较性术语去概念化司法证明是正确的。这正是法律制度处理这一问题的方式。事实认定者的注意力,集中在双方当事人希望进行诉讼的事项上,而不是从上帝视角来看待诉讼场景。
然而,克莱蒙特教授随后做了一个不那么明智的进一步分析活动。为了将其观点与我们的区分开,他声称,司法证明涉及对原告案件理论与其否定命题的逐项要件比较,这种比较是根据“信念函数”来概念化的,并且,在该信念函数中,要件的信念与该要件之否定的信念不需要相加为1。通过逐个要件进行相关的比较,克莱蒙特直接重述了他试图解释清楚的合取难题。关于要件的事实不确定性,将产生概率性后果。错误将作为对单个要件假阳性的错误之后果,不断积累来反对被告。这与起初产生问题的效果是一样的。我们认为,克莱蒙特教授是正确的,即法律制度的作用是减少这种麻烦的现象,但它是通过采取相对似真性而不是对单个要件采用信念函数来实现的。
尽管克莱蒙特教授在许多问题上的分析都富有洞察力,然而,他关于模糊集合和信念函数的应用,无法解释证明标准。他的分析带来了一系列问题:魔法般地改变外部世界的认知;错误适用模糊集合理论;将事实认定与法律术语含义的确定混为一谈;以重述其本来试图避免问题的方式适用信念函数。
虽然我们认为,我们已经论证了克莱蒙特理论的分析性困难,但我们还是想指出他的一些价值。他对复杂主题的博学阐述简直令人感到震惊。另外,从模糊集合论的角度去思考模糊法律术语的含义是有趣的,而且或许是有用的。但是,由于本文所列出的这些原因,他试图提出一种比相对似真性更好的解释,并没能成功。
结论
回到我们开始的地方,我们当然认为,相对似真性理论是关于司法证明一般性质的可获得的最佳解释。经过数十年的尝试,没人能够为强劲的概率性解释提供一个合理的根据。尽管该解释在某些方面具有说服力,但它没有尊重以西方法律制度为例的人类实际状况。该理论要求得太多,远远超过人类所能提供的,并且无法适应人类实际的认知实践。它也无法解释司法证明的许多方面。或许是感受到伴随强大的算法解释的消亡而来的失意,其他学者都在尝试构建基于同样算法的不同解释,但是,出于那些我们已经论述过的原因,他们无一例外也都失败了。相反,相对似真性具有强大的解释价值,能够对诉讼过程进行许多解释。支持相对似真性的其他标志是,其只与司法证明的琐碎方面不一致,因为这些方面是实际存在的,且接受而非排斥人类的认知实践。最后,没有一种普遍理论可以解释复杂适配过程的所有方面。因此,相对似真性是迄今为止为司法证明所能提供的最佳解释。
